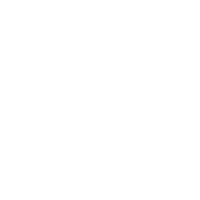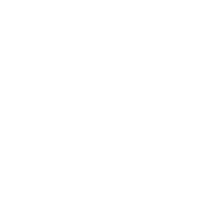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
 发布日期:2023-06-21
发布日期:2023-06-21  浏览量:62
浏览量:62
沈文倬
一
《禮經》在兩漢衹有今文學。今文《禮》立于學官較《易》《書》諸經爲晚;立學前的傅授源流;禮家述說尚有分歧;立學後的分爲三家;史書记載又多失實。這是需要認真考證的。然而;探索今文諸經傳授有個前提;就是先要弄清楚漢初今文經是怎樣形成的。對于這個問題;過去學者們似乎没有感到有進行討論的必要;但要是提出來詢問;可能又都作不出明確的答案。而今文《禮》由于傳習者十分落寞;這方面更加不容易講明白。因此;在全面探討漢初怎樣形成今文經的基礎上;進而考查今文《禮》的傳授源流;對兩漢經學發展的研討;無疑是很有裨益的。
兩漢經學所謂今文、古文;最初衹是指用不同書體繕寫的經文基本:前者是漢隸書本;後者是六國文字魯本。由于發現了六國文字繕寫的經文書本;人們不易辨認;混稱之爲古文;與古文相對而言;才有把已經流傳了的漢隸書本稱之爲今文。(如《史记·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這種古文經本;本來就是秦始皇爲“書同文字”而發動焚書事件時被搜繳銷毀並頒律禁止的書本。漢惠帝解除挾書律、即撤銷了秦朝的禁令之後;《五經》經師逐漸公開傳習;朝廷和諸侯王不断收集到秦時藏匿起來的用六國文字繕寫的各種典籍;其中部分在民間隸定、傳抄;于是才有今文、古文的區分。經之分爲今、古二本;事實上是秦朝“書同文字”的結果。這樣看來;從兩種書本的某些不同字句上產生不同解說、從而分成不同學派;那是以後的事情;最初名之爲今文、古文並不是從經學分成兩個對立學派所引起的。
“古 文”是一個涵義不很明確的名詞。司馬遷說:“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史记·太史公自序》)。似乎没有考慮到秦時撥去的古文究竟與東周以前的文字有無差異。而東漢許慎則以壁中古文與鼎彝文字“皆自相似”(《说文解字叙》);鄭玄亦以爲《尚書》出于屋壁“皆周世象形文字”(《書序》孔疏引《書贊》);他們都把古文與西周文字等同起來了。兩漢人既没有追根究底;以後自然更加含含糊糊地相傳下來; 直到近代才有人經過研究辨析而逐漸把它弄清楚。近百年來;隨着地下實物的大量出土;古文字學起了巨大的變化。根據甲骨卜辭、銅器銘刻、竹木简片、帛、刻石以及璽印、泉幣、符節、玉器、陶器、兵器上變鑄刻或非寫的字;通過對比不同形體而理解到:從殷、西周到戰國;文字在不断變易之中;誠如唐蘭氏所說:“西周文字;幾乎每個王朝都不很一·樣”;“春秋以後;(各國)幾乎各有各的文字”(《中國文字學》)。即如郭沫若同志持“西周官方文字大體上一致”之說;到底還是承認:“晚周的兵器刻欸、陶文、印文、帛書、简書等民間文字;則大有區域性的不同。中國幅員廣闊;文字流傅到各地;在長遠的期間發生了區域性的差别”(《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可見自殷至西周既有縱的變易;到春秋戰國又發生了各國間同時並存的異體。學者們在研究古文字變易的基礎上;很自然地對經書的古文;獲得較爲正確的認識。王國維氏首創古文爲六國文字之說(見《觀堂集林·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而唐蘭氏則更直截了當地說:“長沙發見的(帛片)是楚文字;汲冢是梁文字;孔壁是魯文字。”用以區别于秦文字來說;兩家之說都是正確的。但是;王氏考定古文爲六國文字是爲了證明戰國文字分屬東土、西土兩係;既無視六國之間文字存在同樣大的差異;又缺乏深考而把燕、趙、齊、楚的文化歸屬于同一係統;二者都顯與事實不符;文字分隸東土、西土兩係之說是存在頗大程度的片面性。至于唐氏之說;既没有對古文作全面的考察;也就没有注意到經書的古文除了孔壁、魯淹所出外;還有河間獻王所搜集到的古文;無法断定出于何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漢朝廷所得而以後藏于中秘的;更難考查其來源;而伏勝壁藏的古文《尚書》究係齊文字抑是魯文字;似乎没有分别的必要。因此;說孔壁是魯文字是可以的;把所有古文經書一一查明其爲某國文字;顯然是不可能的。唐說失于狭窄;亦不可取。根據許慎《說文解字敘》所云“秦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凡不用秦文字書寫的一切典籍都在焚毁或秘藏之列;那末說古文經本用六國文字書寫;應該比較妥貼。但必須明白指出:我們承用王氏的名稱;並不接受他東西土兩係之說。
依據《史记·秦始皇本紀》的记載: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二十八年;始皇帝登琅邪刻石;文中亦云:“器械一量;書同文字”。三十四年;李斯爲焚書上議云:“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分析上引之文;可見秦始皇焚書的目的有兩個:一個屬于意識形態方面;即鏟除以古非今思想;也就是鏟除六國儒生非議秦朝新制的思想;另一個屬于政治設施方面;就是與統一正朔、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相適應的統一文字。李斯提議、得到始皇帝“制可”而付諸實施的一係列規定;就是要貫徹這兩個目的。六國史记、《詩》《書》百家語;既是以古非今思想的根據;又是統一文字的障礙;他們不遗餘力地加以徹底銷毁;制訂了實施棄市、族、黥爲城旦等刑罰來懲辦那些不同程度阻礙貫徹焚書法令的反抗者。至于博士官署的藏下不在銷毁之列;不過采用送人秘藏、永禁流通的措施;其用意也是十分明顯的。由于焚書的措施十分周密;六國遗存的史書、經書和百家語遭受到毁减性的摧殘;一部分就永遠消失了;一部分由個别人藏匿而後來重又發現;但或者已殘缺不全;或者已次序錯亂了。秦代焚書給兩漢學術帶來嚴重的禍害;其中最大的惡果是由此引起的經今古文的爭論長期不得解決。
孔壁、魯淹、河間三大宗古文經是在漢景帝、武帝間發現的;而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尚書》;可見那時今文經已經全部流通于世。由此可證今文經形成時期大致在惠帝解除挾書律以後、武帝立《五經》博士以前。但《史记》、《漢書》對今文《五經》的出現;只說某經傳自某人;既没有說明《五經》出現的先後次序;又没有交代第一代大師根據什麽來寫定漢隸經本;這是今文形成過程中至爲重要的關鍵問題;不容許含糊過去。現在;只有聯紧漢初四十多年朝廷和地方上經學流傳狀況;根據每一經開始傅授的各種记載;加以詳密的考辨和恰當的推理;始能弄清具體、確切的事實經過。關于漢初經學流傳狀況;劉歆的《移太常博士書》概括得十分清楚:
漢興;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爟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漢書·楚元王傳》)
我們對今古文没有成見;不會把晚清今文學家所持古文經出于劉歆偽造之說當作定論;因而也不會把《移太常博士营》簡單地斥爲“抵牾鑿枘”而摒棄不議。正確的態度是把上引之文與散見于《史记》、《漢書》等書的有關记載進行對勘;看看與事實是否符合。
一、焚書時頒布的挾書律;雖是秦王朝的措施;但漢承秦制;仍屬有效。朝廷固然“未遑嘏庠序之教”;民間亦未必敢公開傳習《五經》。據《史记·叔孫通列傳》;他初任博土;後升爲奉常卿(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下文一律作太常);太常的職掌是“宗廟禮儀”。其時禮儀殘缺;要他去“略定”;而他所定的漢儀;不過適應高祖“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贵也”的需要;表面上“願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其實是“大抵皆襲秦故”(《史记·禮書》);這位漢儀博士所略定的是秦儀而不是《五經》的《禮》;而高祖要求“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焉之”;更明顯地表明不是重視禮樂。焚書時;《易經》以卜筮之書而被列于“所不去者”;既不禁止;在挾書律解除以前;自然仍用于書卜;不是把它當作經書看待的。《漢書·惠帝紀》云:“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這是因實施大赦、檢查法律而連帶廢除這不易執行的禁止藏書令;並不是爲了提倡經學。對于經學;不僅周勃、爟嬰等“莫以爲意”;而吕后又何嘗在意。《史记·孔子世家》云:“(孔)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太守”(《漢普·孔光傳》作“太傅”。長沙國無太守;(《史记》誤)。這不過秦制太常卿有博士屬官;漢初續置不廢;與叔孫通一樣;孔子襄也不是傳習經書的。據上所論;高祖、孝惠、吕后三朝二十七年中;漢朝廷没有經學。
二、到文帝時代;《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六引《漢官儀》云:“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玄端章甫冠。”這些博士;有的如《史记·封禪書》所云“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有的如《史记·贾誼列傳》所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秦漢之際;《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以及七十子後學所撰记傳、漢人輯爲二《禮记》的;都屬百家語;所以劉歆稱之爲“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既非傳習《五經》;當然談不上經學。但贾誼所通“百家之書”中;包括七十子後學所撰记傳之篇;亦即今存《新書》中與《大戴禮记》相同的篇章。由于他博通紀傳;故劉歆稱之爲“在漢朝之儒”。固然;文帝曾注意到《尚書》;下詔非給太常卿訪求唯一的《尚書》學者伏勝;《史记· 鼂錯列傅》云:“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漢書》“家令”作“遷博上”。鼂錯本來“學申商刑名”;而受《尚書》還朝廷上書;首言“人言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数也”;並没有“以《書》稱說”。《史记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出序》云:“齊人事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可見他的受《書》不過虚應故事;而學《告》的時間也很短暂;即使他曾由太常掌故提升到博士;也決不可能成爲《尚書》的專經博士。《史记·儒林列傅》云:“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這是容禮;徐生父子善容而不通《禮經》;它與《禮經》的聯繫與區别;留在下文討論。文帝時並無《禮經》。這時;《春秋》還没有興起。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中;朝廷衹有《詩經》。《漢非· 楚元王傅》云:“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文帝時曾立過《詩經》博士。又:“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元王子)宗正上邳候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據《史记·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元王死于文帝元年;夷王郢客在二年嗣立;然則申公任博士即在元年;失官而隨郢客歸楚在二年;魯《詩》之立;祗有一年或不到一年。申公大部分傅授魯《詩》的活動仍在楚都彭城和受楚王戊“胥靡”而歸魯家居時;《史记·儒林列傳》云: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漢書》作“韓嬰”。)關于韓嬰的记載僅見此傳;無法考定其始任博士至博士罷官究在何年。《史记·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韓婴任常山太傅在中五年後。既不是由博士遷;可見在文帝時已離開太常。《後漢書·翟酺傳》云:“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五經當作“一經”。文帝衹立《詩》博士;初任申公;申公不久失官;後改任韓嬰。
三、到景帝時代;《史记·儒林列傅》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漢皆》無“生”字)不知始任在何年。後因論老子替得罪置太后;“能之;居頃之;拜爲清河王太傅”。據《五宗世家》;封清河哀王乘在景帝中三年;轅固生罷博士官應在中三年前;然則齊《詩》之立;亦不過五、六年。文、景之際;《五經》中衹有《詩經》立爲博士;經學剛興起;今文三家《詩》的異同未必爲很多人所詳悉;不同派别還未明顯對立;而三家第一代弟子又未能繼其師爲博士。據《漢書·儒林傳》;魯《詩》方面固然有申公弟子爲博士十餘人”的记載;但都在楚都彭城或歸魯家居時所教授;以後如孔安國爲《尚書》博士;徐偃爲《易》博士;俱在武帝之世;且無一《詩》博土。至于《王式傳》所謂“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那是瑕丘江公之孫;不是申公的弟子。關于齊《詩》;轅固生傳夏侯始昌;始昌没有擔任過博士。關于韓《詩》;韓嬰傳淮南賁生和河間趙子;也都没有擔任過博士。綜上所述;申公、轅固生、韓嬰先後任《詩》博士;能官後其職暫缺;當時没有三家並立的事;故劉歆稱之爲“《詩》始萌芽。
景帝還立過《春秋》博士。《史记·儒林列傅》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書·儒林傅》云:“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孝景博士。”均無法考定其始任博士至博士能官究在何年。劉歆提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均指武帝時事;則此時公羊學尚無成就可资論述。文景時雖相繼立《詩》《春秋》博士;但正如《史记· 儒林列傅序》所云:“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寶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土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没有探取什麽措施來發展其學術;不過名義上在太常屬官中增加兩個經學博士而已。其實;當時諸博士的“具官待問”;完全由博土官制度本身決定。漢初博士的職掌仍然沿襲秦制的所謂“通古今”;也就是在它專業知識範圈内備皇帝的顧問。文、景時代增加《詩》、《春秋》博士;與以前的傳记博士性質並無不同;轅固生與黄生在景帝前爭論湯武受命;就是“通古今”備顧問的例證。從制度上看;這時候博士還不是教育官;自然不可能在太常官署傳授弟子;因此申公等《詩》、《春秋》今文大師;雖曾一一度擔任博士官;而他們的傳授弟子仍然在民間。根據這一情況;可證自高祖到景帝這六十多年中;燼管立過經學博士;實質上經學始終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視。
經過史書记載的核實;劉歆論述的漢初經學流傳狀況;基本上符合事實;是可以信據的。而漢初經學衰落的癥結所在;也昭然若揭了。
二
上論漢興六、七十年朝廷經學衰落;而作爲西漢官學的今文經學和它的《五經》漢隸書本;就在這段時間;在齊、魯、燕、趙民間先後形成。《史记·儒林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漢書》改《五經》次第爲《易》、《書》《詩》、《禮》、《春秋》)自惠帝解除挾書律後;那些在焚書前傳習經書、有的還擔任過秦博士的儒生;開始在民間傳授弟子、講說經書。司馬遷所稱“言”字;當訓爲“講說”;就是用《五經》書本解說其義。但當時《五經》書本有存有佚;第一代大師開始傳授也有先後;《五經》寫成漢隸書本和建立師法;情況不完全相同;因而這“言”字所含内容也就不一樣了。可見司馬遷、班固對這個今文經學的形成過程;缺乏足够的認識;叙述强求一律;過于含糊;不得要領;需要作詳盡的推比和闡發。
(一)《易經》 李斯爲焚書上議最後一條是:“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些都是民間日常實用之書;不問可知;大部分是秦文字書本;而内容又不會牽涉當時的思想政治問題;故不在銷毁之列。但究竟哪些書屬于此類;已無法詳考。《漢書·儒林傅》云:“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甚;獨不禁;故傅受者不絕也。”此文不見于《史记》;而“《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史记·太史公自序》);歷來用于筮卜;可知《漢書》的记載是根據事實的。但班氏演述不够確切;後人往往根據此文而認爲秦火後《周易》經學傳受不絕;那完全是誤解;班氏並無此意;衹要看《藝文志》的记載就明白了:“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傅者不絕。”易“書”爲“事”;意義並無大異;而界線比較清楚;“傳受不絕”實指筮卜之事。《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太)常;秦官;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筮卜之事原屬太常屬官的職掌;傳受自在官署。本來;既因筮卜之事而不禁其書;以後其书也衹能用于筮卜;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易經》儘管没有被銷毁;作爲經學的傅習;這和《詩》、《書》一樣;在秦、漢之際也是中斷了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有必要作以上的辨析。還有;焚書也是爲了“書同文字”;豈能容忍六國文字書本的繼續流傳;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大部分是秦文字書本;當然也應有一部分六國文字書本。規定“不去”的自以秦文字書本爲限;對六國文字書本不是銷毁也得送人秘藏;禁止流通;《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可證。焚書議雖没有具體交代;根據事實推理;相信他們會這樣處理的。當時的秦文字指篆書、隸書。《晉書·衛恒傅》載衛恒《四體書勢》云:“隸書者;篆之捷也。”郭沫若、唐蘭二氏均以爲篆書寫得簡易、草率即成秦隸(漢隸)。然則秦火中保留下來的《秦紀》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是秦隸書本。由此得出結論:《易經》在秦火前就有隸書本;到漢初用不着隸定改寫。《五經》公開傳習;經師就可以用這種本子來講授了。
《史记·儒林列傳》云:“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漢書·儒林傅》云:“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颜注:“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徙關東大族事在高祖九年十一月;田何是生于秦火以前的齊國人;幼年學《易》;用六國文字書本。至漢初;他是傳《易》第-一代人師;當時已有現成的隸書本;用以教授;不必另行隸定。他没有撰作章句解說;因而未成師法。漢人所說某經師法即指傳經某師所撰的章句解說;如“(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見《漢書·儒林傳》);是其明證。田氏弟子周王孫、服生;再傳弟子楊何;都著有《易傳》;而《漢書·儒林傳·贊》记武帝所立《五經》博士有“《易》楊”之文;可見至楊何時開始建立師法;完成《易經》今文學。
(二)《春秋》 漢初《五經》第一代大師;《詩》之申公、轅固生、韓嬰;《書》之伏勝;《禮》之高堂生;《易》之田何;都生于秦火之前;有的還是秦始皇的博士;幼年學經;用六國文字書本。惟獨《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江公;生于文帝時代;没有經歷秦火;其學何人所授;其書本從何取得;司馬遷、班固均不詳悉;其間史事必有闕漏。
《春秋傳》除《左氏》古文不論外;《公羊》在景帝時出現;到武帝元朔元狩間出現《穀梁》。《公羊解詁序》徐彦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傅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公羊傳》隱公二年何休注:“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於竹帛。”東漢人所述《公羊傳》傳授係統;近人都不敢輕信。而蘇輿著《董子年表》;根據莊公三十二年、 昭公元年傳“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句;以爲“秦二世時已有‘人臣無將’語;見《史记·叔孫通傳》;又《公羊傅》成于秦前之證。”就以上记載綜合評議;《史记》所載“人臣無將”句;尚不屬原文徵引;意義亦微有差異;持此孤證;不足爲《公羊傳》成書于秦前的依據。但不應抹煞它與《公羊傳》義有某些聯紧;作爲公羊氏世代口授傳說;倒是個合適的旁證。司馬遷既以爲胡毋生始傅《春秋》;何休注《公羊傳》也承認胡毋生著于竹帛;戴宏所述;大致可信。據以論定:《公羊傳》是公羊壽受先代口授大義;由弟子胡毋生寫成其本。它在晚周尚未成書;到漢景帝時才用漢隸寫定;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
《史记·儒林列傅》云:“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史记·平津侯列傅》云:“(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他受胡毋生之本在景帝初年。又主父偃學《春秋》亦應受胡毋生之本;《史记·主父列傅》云:“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主父日:臣結髪遊學四十餘。”立衛后在元朔元年;燕王自殺在二年;據以上推;他生于吕后時代。又:“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學《春秋》至遲在景帝中年。那末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見《史记·儒林列傳》;下同。(《漢書·董仲舒傳》襲《史记》之文而作“少治《春秋》”;恐屬臆改);學《春秋》也應在景帝初年。《漢書·儒林傳》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皆稱其德。”亦受胡毋生之本。凌曙《春秋繁露注序》云:“自高至壽;五世相承;師法不墜;壽乃一傳而爲胡毋生;再傳而爲董仲舒。”其說不知所據。公孫弘、主父偃、董仲舒與胡毋生行輩略同;並無師承關孫;三人不過用其所寫定之本來研習推闡而已。胡毋生“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仲舒“以修學著書爲事”論成就以董氏最爲卓著;所以說“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公羊傳》書本雖定于胡毋生;撰解說、完成今文學師法則出于董仲舒。
《穀梁傳》晚出;《史记·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語極簡略;而《漢書·儒林傳》叙述較爲詳明: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傅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江公呐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申公傅《春秋》和江公受學于申公事;均不見于《史记》;很難考實。元朔五年;公孫弘爲丞相;六年;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次年即元狩元年;立皇太子;二年;公孫弘死;所以蘇輿《董子年表》係二家議《春秋》事于元朔六年。《穀梁傳》出現于此時是確實的;但它的撰人和傳授諸問題;說者多分歧;一直没有論定。《穀梁集解序》楊上勛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于子夏;爲經作傅。傅孫卿;孫卿傅申公;申公傳博土江翁。”此文本應劭、桓譚、阮孝緒之说而以意補苴;所稱子夏三傳至申公顯屬謬誤:1·據《史记·仲尼弟子列傅》;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孔子死時子夏年二十九;又據《史记·荀卿列傳》所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李園殺春申君在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即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子夏、穀梁赤、荀卿縱然都是高齡;要穀梁赤受于子夏而又傅于荀卿;顯然是不可能的。2·據《史记·儒林列傅》;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趙)綰、(王)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迎申公;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據以上推;申公生于秦始皇二十年前後。荀卿生卒年雖無法考實;據應劭《風俗通·窮通篇》所云“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土于稷下;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與《史记·荀卿列傳》所云“年五十(當爲十五之誤);始來遊學於齊”;適相吻合;自屬可信。姑以齊威王卒年爲準。威王卒于周慎靚王元年(公元前320);到秦始皇九年;計算起來荀卿已近百歲;要他在秦火前一二年間授經于申公;無疑也是不可能的。至于穀梁赤爲經作傳;亦不可通: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爲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其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2·僖公二十二年傅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是用孟子語;見《離婁上》。豈有子夏弟子著書而引及《孟子》之說者。凡以上所論;都可以證明楊疏誣妄;不足信據。當然;《穀梁傳》作者事實上還不止出于孟軻、尸佼之後的問題;從傳文觀察;到處可發現它根據《公羊傅》而撰作的證據。陳灃《東塾讀書记》卷十《春秋三傳》論述這一問題甚爲詳備;舉證最堅實的有下列幾點:1·莊公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傅》云:“邾婁邑也;曷爲不擊於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則云:“公子贵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日君在而重之也。”2·文公十二年“子叔姫卒;貴也;公子母姊妹也。其一傳日:許嫁以卒之也。”很明顯;所稱“其一云”、“其一傳云”都是《公羊傳》之文。3·陳氏云:“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毎年祇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4·“陳氏又云:“《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於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云云;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说爲是而録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说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陳氏舉證中以一、二兩項最具典型意義:二傳義異;而《穀梁》附存一说却與《公羊》相同;實是《穀梁》成書在《公羊》之後的鐵證。此外;還可補充一證;定公元年《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而《公羊傳》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日:‘定君乎國;然後即位。”昭公于二十五年謀伐季平子失敗;出亡于外;三十二年病死;次年從乾侯遷柩歸魯。《儀禮·既夕》遷柩朝祖節“正柩于兩楹間”;是將葬朝祖之禮。“正棺”是记其禮事(何休、范寧之注均誤);”定君乎國”才是沈子的經義。《穀梁》顛倒其文;恰恰是襲用《公羊》而復有誤失的證據。以上俱屬内證;是十分確鑿可據的。那未究竟是誰的著作呢?近人金德建氏立一說:“試看《史记·儒林列傳》便曾這樣地說過:‘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爲’字應該當‘作’字解釋;這就明白地說《穀梁傳》這部書是瑕丘江公所作”。(《司馬遷所見書考·瑕丘江公作穀梁傳的推測》金說是對的;《漢書》改“爲”作“受”;把原意歪曲了。這樣說來;《穀梁傳》是江公採用當時經師口頭相傳的一些經義、並參照《公羊傳》而编寫的一部仿作。它既在景、武間用漢隸寫定;也是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
公羊《春秋》雖在景帝時曾一度立爲博士;但到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時;武帝命江公“與仲舒議”;對二者的選擇;本來並無成見。由于公孫弘的“集比其義”;《穀梁》没有能取代《公羊》;從此“其後浸微”;衹在民間傳授。據《漢書·儒林傳》记載;江公傳榮廣、皓星公;榮廣傳蔡千秋、周慶、丁姓。到宣帝甘露三年石渠會議中;“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因爲“上(宣帝)善《穀梁》說”;而“《公羊》家多不見從”;不得不打破一經一師法的爲面;開創了一經幾個家法並立的設置;《尚書》、《易經》各立三個博士;而《春秋》亦在《公羊》外增立《穀梁》博士。這時候周慶、丁姓“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看來要到“慶、姓皆爲博士”;才得完成《穀梁》今文學。
《漢書·藝文志》云:“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班固明白指出;解說《春秋》的记傳;都是依據經師們先後口頭傳授的經義以记錄成書的。上文考證的結論也證明了這-點。由此可見;在文、景、武三朝爲《春秋》作傳的有好幾家;《公》、《穀》二傳都是西漢經師的著作。
又:“《春秋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 《四庫全非總目提要》云:“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傅》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傅》附經;則不知始於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别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傅》亦無經文;足以互證。”然則《春秋經》十-卷的漢隸書本;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班固自注:“公羊、穀梁二家。”依經作傅;經文都被引述于傅文之中;亦即出于傅者口述。《公羊》、《穀梁》二傳寫成告本;經文的絕人部分亦隨之隸定了。二傳字有不同;故經文字亦有不同;班固自注稱爲“二家”;就是二傳引述經文字有異同的意思。
(三)《尚書》 伏勝是西漢傅《尚書》的第一代大師;如上引《史记·儒林列傳》所述;他是秦博士;當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而找到他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故命太常掌故鼂錯去受學。據《漢書·鼂錯傳》;他受《尚書》還;改官太子舍人、太子門大夫;不久又升爲太子家令。文帝前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鼂錯對策稱“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以此核定文帝求能治《尚書》事當在前十一、二年。據以上推;伏勝當生於秦昭王五十年前後。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他已四十多歲(康有爲說“年已六七十矣”;是錯誤的)。《史记·儒林列傅》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数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康有爲斷此文爲“劉歆竄亂以惑人者”;他說:“伏生爲秦博士;秦雖焚書而博士所職不焚;則伏生之本無須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則壁藏亡失之說更不待攻。”(《新學偽經考·史记經說足證偽經考》)康氏爲了否定《漢書》所记孔壁古文;遂並《史记》所记伏勝壁藏亦歸之劉歆竄亂;空言無據;顯屬誣妄。“博士官所職”不焚(康氏故意删去官字);自指博士官署所藏之書而非私人藏書;伏勝是治《尚書》的專門家;故私人持有六國文字書本;他在焚坑事件中没有觸及;怵于“黥爲城旦”之禍;又不願把藏本繳銷;砌在屋壁中以求保存;實屬事理之必然;竹木簡書本體積大;在戰亂中散失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史记》此文絕無可疑之處。二十九篇六國文字書本既在伏勝手裹;以後在齊、魯間用以教授;就由他根據此本隸定;王國維氏《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云:“其傅授弟子則轉寫爲今文”;是完全正確的。
齊、魯間學者“無不涉《尚書》以教”;伏勝的弟子應該很多;而知名者衹有兩人:一是歐陽生;一是張生。《史记·儒林列傳》云:“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漢書》明下有“定”字)張生何時爲博士;伏生孫何時被徵;史無明文。《漢書·藝文志》云:“《傳》四十一篇。”《玉海》卷三十七載《中興書目》引鄭玄《尚書大傳序》云:“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乖;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闻;以已意彌縫其闕;别爲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爲《傳》。今殘存《尚書大傳》是張生、歐陽生记其師之說;《尚書》今文學事實上完成于伏勝。
(四)《詩經》今文《五經》中《詩經》最爲特殊;六國文字魯本在秦火中没有被遗留下來;惠帝解除挾書律後;秦時的儒生憑记憶、默誦口說;于是在不同地區出現三個文字有所不同的漢隸書本。《漢書·藝文志》云:“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經》在秦前本是用于音樂、舞蹈的樂曲;有韻便于歌詠;章什多重句容易记憶;因而它不像《書》《禮》那樣亡佚了一部分而獨得保存全經。
先述魯《詩》:《漢書·楚元王傅》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别去。”漢高祖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秦火時已四十四歲。元王死于孝文帝元年;但不知其年壽幾何;故生年不可知。與高祖異母;相距至少在十五歲以上。上文考定申公生于秦始皇二十年前後;秦火時不過十三四歲;因而元王等從浮丘伯受《詩》不能早于秦火前二、三年。申公童年初學;没有學成;到挾書律解除後赴長安再次從浮丘伯“卒業”。當年浮丘伯所持以教元王等用的是六國文字書本;無疑在秦火時已繳銷焚毁了。“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不言可喻;他們在長安傅受時;由浮丘伯默誦口說而由申公记錄寫成漢隸書本。司馬遷撰《楚元王世家》不记元王父子學《詩》事;撰《儒林列傳》不记申公先後兩次從浮丘伯受學事(衹說“吕太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客]同師”);即使前後史實銜接不起來;又導致含糊地作出“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帶有片面性的判断。這和他撰《五宗世家》不记河間獻王從民間得“古文先秦魯非”和魯恭王壤孔子舊宅得“古文經傅” 一樣;俱屬見闻疏漏的結果;既不可據;亦不足怪。
《史记·儒林列傅》云:“(申公)歸魯;退居家教; 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傅。”《漢書·儒林傅》訓下增“故”字;不重“疑”字。《史记索隱》根據這不重疑字之文而斷爲“申公不作詩傅”;其實是不對的。二傅字都是動詞;疑者不得確解之意;作訓故教授的原則是“無傅疑”;遇到不得確解的地方;寧阙不傅授。《漢書·楚元王傅》云:“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顏注:“凡言傳者;謂爲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漢書》二傅不應自相矛盾;顯係前者傳寫誤脱疑字。申公確曾撰作《詩傳》。姚振宗《藝文志條理》王先謙《漢書補注》都以爲“申公爲《詩傳》”即是《藝文志》所列的《魯故》。這樣說來;在吕后時代;申公即承師說撰《魯故》而完成魯《詩》今文學。
次述齊《詩》:據《史记·儒林列傅》;武帝建元元年“復以路良徵固”;“時固已九十餘矣”;上推秦火時已二十餘歲;幼年學《詩》;自用六國文字書本。“諸齊人以《詩》顯贵;皆固之弟子也。”齊《詩》的漢隸書本是他默誦、记錄下來的。《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王先謙《補注》云:“此謂齊、韓二傳推演之詞;皆非本義;不得其真耳。”姚振宗《藝文志拾補》云:“轅固爲之傳;而其書不見。”又引荀悦《漢紀》“齊人轅固生爲《詩外内傳》”而作按語云:“轅固生作《外内傳》唯見於此。《藝文志》所謂‘取《春秋》採雜說非其本義’者;似即指兩家外傅而言;則實有其善也。”轅固生著作雖不見于《藝文志》著錄;但據王、姚二氏的闡述;他也曾解說《詩經》;從而建立齊《詩》師法;由他來完成今文學的。
再次述韓《詩》:《漢書·儒林傅》所云“武帝時;(韓)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不知在何年?蘇輿《董子年表》擊于元朔三年;大致可信。他在文帝時與申公先後立爲博士;而“韓生孫商爲今上(武帝)博士”;可見與董仲舒論難時已在高齡;推算起來;其年與申公相仿;生于秦火前;童年學《詩》;自用六國文字書本。“其語頗與齊、魯間殊”;漢隸書本是由他默誦、记錄而寫定的。“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外傳》尚存;在他手裏完成韓《詩》今文學。
轅固生、韓嬰兩人的經學傳授活動雖不甚詳悉;但漢隸書本的寫定、《詩傅》的撰作這兩個主要問題還是很清楚的。
經過以上的考查;對《易》《春秋》《書》、《詩》四經今文學的形成過程已基本上弄清楚;確實;它決不如過去學者們想象那樣簡單;而且《禮經》的成學;情況還要複雜;這將在下章闡述。總起來說;今文經的形成包括兩個内容;一是漢隸書本即今文經本的寫定;二是隨之而來其經師法的建立;比較起來前者更爲重要。《易經》用于卜筮;“書同文字”以前即有秦隸書本;《春秋經》是隨着文、景時人撰作《公羊傳》、《穀梁傳》一起用漢隸寫成的;《尚書》根據壁藏六國文字書本改寫隸定;完成于惠帝、吕后之間;衹有《詩經》在三個地區各自由儒生默誦口說而记錄成漢隸書本;出現縱有先後;不會遲于文帝初年。漢隸書本寫定以後;大師們在民間傳授弟子;各經師法逐漸建立;爲漢武帝獨尊《五經》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兩漢經學才得從此進人興旺時期。至于成學以後的師承傳授和家法分途;就四經而論;《史记》、《漢書》、《後漢書》的记載比較翔實;没有重加論列的必要;本文也就不再重複這方面的問題了。
三
《史记》、《漢書》记述《禮經》今文學的形成過程;疏漏缺略;前後刺謬;頗難董理。《禮經》傳自高堂生;而馬、班都不爲高堂生立傳;事跡不詳。《史记索隱》引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他經歷秦火;幼年學《禮》;自用六國文字書本。據焚書議;《詩》、《書》是焚、禁的主要對象;《春秋》》是魯史;應在“非《秦紀》皆燒之”中;《易》以卜筮之書列于“不去”;百家語不應包括經書;《五經》中祇有《禮經》没有明文見于禁令。《史记·儒林列傳》云:“本禮(本字與禮字連文;说見下文)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至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禮樂志》云:“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遭秦滅學;遂以亂亡。”《禮經》曾否被焚、禁;二書既含糊其詞;對士禮的來龍去脈;更未交代清楚;這兩點很難落實。《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加上篇數; 頗失《史记》原意;又把問題攪亂。這些都是不易解決的難題。
大家知道;《詩》、《書》、“禮”、“樂”是儒生專門修習的科目;是不分主次的;“禮”傳自齊、魯;而秦朝又別創禮儀(見《史记·封禪書》、《禮書》、《漢書·禮樂志》;說詳下文);從制度上看兩者是對立 的;因此;無論怎麽說也不可能把它置于焚、禁之外。《論衡·短謝》云:“秦燔《五經》;坑殺儒士。”說《五經》一起焚毁;惟見此文。上文已論定《易經》的六國文字書本也在焚、禁之列;那末王充此說雖出後世傳聞;倒頗能反映焚書真相。由此可證《禮經》的搜繳銷毀是無可置疑的。之所以成爲難題;其原因在于它的情況遠比《詩》、《書》複雜;衹有從它的特點上去探索;方能弄明白。上述這些問題。“禮”與《詩》、《書》不同;《詩》、《書》是文字记錄的書本;而“禮”是人們實行各種禮典的具體儀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經常舉行各種禮典;他們必須自幼學習;成人後又長期實行;十分熟悉;在當時不需要记錄成文。春秋以後;周王朝日漸衰落;諸侯國都出現權力下移的傾向;相應地在制度上發生僭上的現象;舊制度被新執政者所破壞;造成了“禮壞樂崩”的爲面;某些統治者爲了防止它的湮滅;才有必要撰作書本;以利保存。大約在魯哀公到魯共公這一百多年中;自孺悲受哀公命從孔子學士喪禮開始;孔氏弟子或後學相繼論次;陸續寫成《禮經》書本若干篇(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證;見《略論禮典的實行和《禮經》書本的撰作》)。司馬遷所說“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就是各種禮典在孔子時還没有寫成書本的意思。《禮經》成書以後;凡提到“禮”時;在理解上固然包括禮典、禮書二者在内;但禮典給人的印象較爲深刻;大家心目中仍然以它爲主體;秦火中如果“禮”也被當作主要對象的話;勢必以禁止舉行禮典爲首要任務;其次才是焚禁《禮經》書本。可是;那時候大夫以上的禮典已經逐漸廢棄;事實上用不着大事張揚;所以没有必要在焚書議中特立“禮”這個項目;因而對《禮經》書本也相應地没有加以更多的注意;很可能與百家語等應毁之書一起處理了。《史记》稱“書散亡益多”;《漢書》稱“遂以亂亡”;都是說《禮經》在秦火中亡佚了大部分而没有全部焚毁的意思。
禮典是按爵位尊卑來分别的。因政治變革而被廢棄的都屬大夫以上的禮典;士禮接近民間;與民風土俗聯繫較多;又不存在僭上的問題;不可能也不必要禁止其舉行;在秦火中没有受到影響。今存《禮經》十七篇中;;士禮書七篇;即《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上下篇(下篇題《既夕》、《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喪服》雖說“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滕文公下》);但天子絕旁期;大夫無緦服;衹有土具備五服;它基本上屬于士一級的。還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兩篇;當時稱之爲“鄉禮”; 是鄉大夫、州長等地方官在民間推選“處士賢者”;並會民習射;以觀其能。雖屬大夫禮而其事接近土庶;等級並不森嚴;與士禮相仿佛。《史记·儒林列傅》云:“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大射當作鄉射;劉、項戰爭剛結束;鄉禮隨即恢復。據以推證;冠、昏、喪、祭等士禮與庶人之禮差别不大;關係尤爲密切;在民間照常舉行;從未間斷過。司馬遷所說“於今獨有士禮”;既是指仍在民間實行的八個禮典和喪服;同時也是指被保留下來的十篇六國文字書本;並且它隨着“書同文字”的實施;不言可喻;已在民間改寫爲漢隸書本了。就禮典言衹有八個;就書本言却有十篇;他在士禮下没有標明篇數是毫不足怪的。但後來據以演述的记載不知何所據而加上篇數?班固說“《士禮》十七篇”是從劉向那裏抄來的。荀悦《漢紀》(卷二十五)云:“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多不備。”班的十七和劉的十八以及王充的“見在十六篇”(見《短謝》篇);不過是上下篇分合所引起的差異;不必深究。十七篇明明包括天子禮一篇、諸侯禮四篇、大夫禮兩篇(“鄉禮”兩篇除外);禮典處處講究爵位等級;豈容以卑統尊而總稱之爲“士禮”!由于劉向對禮學不太在行;在典校經傳處理今文經師所傳之本時;没有弄明白“獨有士禮”的相對意義;冒用《史记》所稱“士禮”之名;導致後世禮家以訛傳訛;說漢初《禮經》又名《士禮》;這後果是很嚴重的。《禮记·奔喪》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改傳爲得;使司馬遷所說“高堂生能言之”的事得到落實;衹有從民間取得了漢隸經本;才能據以講說傳授。但他同樣没有能分辨被保留下來的衹有士禮這--部分;可能受劉氏的影響;對高堂生取得七篇天子諸侯大夫禮的事仍然說不清楚;可見鄭氏對漢初今文《禮》的形成也失于深考。
關于七篇天子諸侯大夫禮的來源問題;司馬遷没有提及;如上文所論;他述魯《詩》不记申公從浮丘伯受學;同屬見聞疏漏所致;既不可據;亦不足怪。張淳《儀禮識誤》云:“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張氏所疑是有道理的;但說高堂生所得十七篇都是士禮;非今存之本;顯屬毫無根據的臆想;不足信據。根據史書记載;高堂生外别無其他傳人可考;我們衹能作這樣的假設:高堂生在秦火前學《禮》;讀過全經;秦火後從民間取得七篇士禮、兩篇“鄉禮”和一篇《喪服》的漢隸書本;在傳授弟子過程中;對佚亡的部分篇章尚能记憶;極力連綴成篇;如《詩經》的轅固生、浮丘伯那樣;默誦记錄而成漢隸經本。可是;《詩經》韻語便于諷誦;而七篇大夫以上《禮》三萬三千九百多字;書誦而無脱訛;有没有可能;還得深人研討。《漢書·儒林傳》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及孔氏;凡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之法。”《漢書·禮樂志》云:“河間獻王採禮樂古事;稍稍増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歴代禮家對《儒林傳》的记載頗多指責;如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云:“若《燕》、(大)《射》、《朝》(當作覲)、《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后倉是武帝、昭帝時人;既没有見過全經;對佚亡的篇章全無印象;自然無從推究;又所持之本不完全是士禮;說他創立“推士禮以及天子”之法更爲不確切。可是;與《禮樂志》的记載聯緊起來考察;就能明白它的真相:一、西漢今文學者都承認十七篇不是全經;不但“倉等”;還有其他“今學者”說經時都曾使用“推致”之法以探究大夫以上的禮;可見這是今文《禮》學者世代相傳的師法;而應該上溯到第一代大師;二、就“推致”之法的内容來檢索;也祗有高堂生最切合;他取得士禮書本之後;才有可能用士禮來推究早年讀過的大夫以上的佚禮。由此可證所謂“推致”之法當是高堂生所首創;后倉及“今學者”們不過承襲成法而已。
高堂生進行“推致”的具體做法;雖無明文可據;但分析十七篇之文;其事本來很易明瞭。第一;《鄉飲酒禮》和《燕禮》同屬飲酒禮;獻、酢、酬、舉觶、以樂娱賓、旅酬、無算爵等節目完全相同;不過器物、儀容有隆殺、繁簡之殊;《鄉射禮》和《大射儀》同屬射禮;三番射事中的納射器、誘射、請射比耦、拾取矢、釋獲、數獲、飲不勝者等節目完全相同;根據《鄉飲酒禮》來推致《燕禮》;根據《鄉射禮》來推致《大射儀》;就能按節比附;易於默誦;何況所謂射禮;不過把射的部分加于飲酒禮中;《鄉射禮》、《大射儀》的前段和後段諸節更是直接抄自《鄉飲酒禮》、《燕禮》。第二;《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和《少牢饋食禮》、《有司》都是祭祀祖先的禮典;除了因爵位不同而引起器物、儀容的差異之外;祀典的主要節目大致相同;自可據前者以推致後者。第三;祭祀饋食用食禮;即先食黍稷(飯)而後飲酒;《公食大夫禮》是“主國君以食小聘大夫”;與饋食禮雖分隸賓、吉兩類;禮意有異;而禮儀則頗多相同;也可按節推究。第四;惟有《聘禮》是諸侯禮;《覲禮》是天子禮;非士禮所可推究;但仍有一些章節可以類比;如《聘禮》禮賓節與《士冠禮》醴冠者節、《士昏禮》赞者醴婦節;同屬有獻而無酢、酬;其儀注還是相同的。第五;至于器物、儀容的隆殺、繁簡;表面上縱然千差萬别;其實因等級而異;祗要掌握其通例(如《禮记·禮器》所云“有以多爲貴”“有以少爲貴”、“有以文爲貴”“有以素爲貴”等);也不難推比而得。高堂生熟于禮儀;根據士禮來推致早年讀過的若干篇大夫以上的《禮》;默誦记錄了其中的七篇;是完全可能的。經過上述各方面的推證;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高堂生在惠帝解除挾書律後;爲了講授《禮經》;從民間取得七篇士禮、兩篇“鄉禮”和一篇《喪服》的漢隸書本;又創立了“推士禮以致天子之法”;默誦记錄了《燕》《大射》《覲》、《聘》《公食》《少牢》《有司》七篇天子諸侯大夫禮;匯輯、寫定《禮經》今文十七篇。
鄭玄《三禮目錄》著錄戴德、戴聖、劉向三家所编排《禮經》篇目次第。戴德的篇次是:《士冠》第一、《士昏》第二、《士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第九、《鄉飲》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從三家不同篇次的對比中;看出戴德编排方法的依據有下列三點:1·士禮七篇排在前面;保持了“獨有士禮”的原目;2·以《少牢》、《有司》置于《士虞》《特牲》之後;以《燕禮》《大射》置于《鄉飲》、《鄉射》之後;以及以《聘禮》、《公食》、《覲禮》置于大夫禮之後;都是“推士禮以致天子之法”的反映;3·《喪服》不是禮典;附列最後。這些;恰恰與上文所論證及其結論若合符契。可見大戴之本即用后倉篇次;也就是高堂生遞傳下來的原编次第。戴聖與后倉、戴德立異;將十七篇次第重行编排;《漢書·藝文志》所列“《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就是后氏與小戴不同的意思。
高堂生所定今文經本不久即已流傳;除弟子傅抄外;如文帝時容禮學者徐延就曾讀過。但高堂生没有撰作解說;師法没有建立起來。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同樣衹是授讀經文。一直到武帝末年;后倉寫成《后氏曲臺记》;立爲博士;才完成《禮經》今文學。
《五經》今文學是在民間形成的。《詩》、《春秋》雖在文、景時代立過博士;但那時的博士都是通今古、備顧問的性質;無論《詩》、《春秋》博士或傳记博士;都没有在太常官署傳授弟子的任務;經師教授仍在民間。劉歆說:“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起於建元之間。”由于田蚡的推動;武帝在建元五年設置《五經》博士;由于董仲舒、公孫弘的鼓吹;又在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到這時候;博士才由顧問官轉變爲教育官;今文經也由此而從民間私學轉變爲朝廷官學。從制度上看;這一性質的轉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四
《禮經》的成學過程既較複雜;因而它的師承傳授和家法分途也迥然不同。由于兩漢學者對“禮”的認識很模糊;既没有分辨齊、魯所傳古禮與以秦儀爲藍本的新制漢儀有何不同;又與漢儀實行中派生的“容禮”混淆起來;以致史家對今文《禮》的傳授;记事頗多失實;家法係統的糾葛亦未一一明辨;而後代禮家又踵誤襲謬;罕有提出異議。對這些問題;自應鈞沉索隱;切實探討;力求回復它的本來面目。爲了便于評述;根據前後期不同的特點;把整個發展過程劃分爲三個階段;從相互比勘中逐一辨析。
今文《禮》傳授的第一階段最爲複雜;祗有弄明白它和“漢儀”、“容禮”的區别和聯繫;才能確定高堂生的傳授係統。
兩漢修訂漢禮儀是史不絕書的。在漢初;第一個要評議的是首創者叔孫通。《史记·叔孫通列傳》云: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漢二年;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说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日:“得無難乎?”叔孫通日:“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採集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日:“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隸(肆);會十月。
叔孫通于二年降漢;五年高祖即位;拜博士當在三、四年間;正是劉、項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漢官九寺大卿雖本秦制;但那時還不可能有此完備的建置;不過用魯職名稱之爲博士。但從制度上看;它已具有太常漢儀博士的性質。定朝儀在六年夏秋之間;還不可能考虑全部漢禮儀;不過適應整肅朝規的急切需要;並迎合高祖“令易知”的要求;倉卒制訂;無疑是很簡陋的。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羣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柬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束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傅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候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传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能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日:“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
《漢書》顏注:“漢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朝歲當屬視朝禮範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無朝禮;叔孫通也不可能别傳古禮。此時九卿逐漸建置;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他當了漢代第一任太常卿。
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尉太子太傅。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
根據《本傳》所載;叔孫通于七年定朝歲儀後升任太常卿;九年改任太傅;至惠帝元年復爲太常;開始定全部漢禮儀。《漢書·郊祀志赞》云:“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高帝時所定朝儀;曾寫成書本並付諸實施;而《漢書·禮樂志》云:“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惠帝時創制其他禮儀則没有完成。《漢書·梅福傳》載成帝時人梅福上書云:“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他不知完成多少篇;而東漢人則记明篇數;如王充《論衡·短謝》云“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後漢書·書褒傳》載章帝章和元年班固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但其數又不同。《禮樂志》又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傅。”因爲書没有撰成;書名既未定;篇數所傅又不一致;看來這個未定稿在他死後曾流散在廷尉官署;後來被班固收得其中十二篇。
叔孫通雖自稱“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但就其所定朝歲儀來檢驗;却絲毫没有古禮的痕跡;相反;探用秦儀則確鑿有據:《禮樂志》又云:“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宗廟樂是祖先祭祀的一個組成部分;祀典用秦儀是無可置疑的。《史记·禮書》云“叔孫通頗有增益减損;大抵皆襲秦故。”他本來主張“三王不同禮”;定漢儀不過利用現成的秦制;結合當時需要來增删;與齊、魯所傳古禮没有任何因襲关系。由此可證;兩漢實行的禮儀;立足于秦制;學者們就不願意去辨别齊、魯與秦兩種文化在制度上的異同;因此史家評述禮學的發展;往往承認“叔孫通制定禮儀;卒爲漢儒宗”(《漢書·禮樂志》);而文帝以後歷朝修訂禮儀;有時也吸收《禮經》學者參加;又往往被說成漢儀異源于古禮;因而使兩漢禮學更加複雜;很難分别。經過對叔孫通事跡的考查;可以據以論定:第一;漢儀根據秦儀增删;既與齊、魯所傳古禮没有因襲關係;就不應該把叔孫通當作傳《禮》的學者;評述《五經》禮學的傳授;絕不容許對他有任何的牽扯。第二;漢代實行的禮儀是排除古禮的;《禮經》衹單純供經學傳授者研習;因此對某些既傳授《禮經》又參加漢儀修訂的學者;應該嚴肅對待;要依據具體情況;弄清楚究竟是《禮經》學者還是漢儀學者。
在漢儀創制和實施過程中;曾出現一個“容禮”;當時很盛行;但與《禮經》傳授頗多瓜葛;而過去禮家没有給以足够的重視;需要縝密探討;以明底蘊。《史记·儒林列傳》云: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傅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由徐氏焉。
《史记》此文晦澀;後人多不得其解。《漢書》移易删節;頗失原意。今略加詮釋如下。“多言禮”;禮字泛指。秦、漢之際;如《史记·封禪書》所說;有齊、魯學者所傳古禮;“(始皇)即帝位;(議封禪;)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議各乖異”;也有秦朝創制的禮儀;“(高祖)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大宰;如其故儀禮”;禮字包括古禮、秦儀和正在據秦儀修訂的漢儀;諸學者中惟有高堂生講說古禮;故稱之爲“最”。今人多誤於“本”字逗;義不可通;當從日本瀧川資言《史记會注考證》于“最”字逗。“本禮”與“經禮”、“正經”同義;都是指區别于秦、漢新儀的古禮;它在孔子時還没有寫成書本;故日“其經不具”。後來孔氏後學把大部分古禮典记錄成文;但在秦火中又有一部分散失亡佚;惟有士禮獨存。“於今”指司馬遷撰傳時;他祗知道士禮幸未亡佚而由高堂生講說流傅的。“善容”;《漢書》顏注引蘇林云:“《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焉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容貌威儀本是各種古禮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著之節;需要善容者才能勝任其事;因此禮典參加者必須講究容貌威儀。從原來的意義上理解;不應該也不可能把禮與容截然分割開來。但是;秦、漢以來;古禮典已不再舉行;殘存的《禮經》書本在漢初衹當作經書供學者們講說研討之用;而新創的漢儀尚未具有完備的規模;所用容貌威儀往往從古禮典裹移植;善容成了個人的特長;可以不知經而在朝廷任禮官大夫、在郡國任容史。這樣;《禮經》書本的傳授者和漢儀的善容者分離開來;成爲兩個並列的係統;所以在此文中“禮”和“容”不是一個東西而分别傳授:徐生、徐延、徐襄和徐氏弟子以及張氏都是傳“容”的;而高堂生和蕭奮是傳《禮經》書本的;“以容”和“以禮”分道而行了。關于傳“容”一係比較清楚;而傳“禮”一係不甚明確;容易引起誤解。文中對高堂生傳給誰和蕭奮受于何人;均没有交代;兩人有無關係就成了問題。近人洪業僅僅根據“《史记》言‘奮以禮爲淮陽太守’句前敘徐氏弟子也;句後又云‘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儀禮引得序》);便把蕭奮断爲徐氏弟子。洪氏没有深入領會司馬遷原意;其說實誤;試爲辨解之:第一;徐生及其子孫、弟子皆言“以容”;而蕭奮言“以禮”;言“以容”者在朝廷任禮官大夫、在郡國任容史;而言“以禮”的蕭奮没有擔任此等職務;兩個並列的傅授至爲顯明;不應混爲-談;足證蕭奮不是傳“容”的學者。第二;蕭奮傳孟卿;孟卿傳后蒼;《漢書·儒林傅》有明文可據。后蒼是傅《禮經》的大師;容與禮既屬不同係統;蕭奮就不可能屬于徐氏弟子。第三;洪氏是單純從《史记》的文氣來作出蕭奮屬徐氏弟子的判断的。可是就文氣而論;倒恰恰證明蕭奮不是徐氏弟子。此文首論《禮經》書本。“於今”兩句是總結上文。下云“而魯徐生善爲容”;徐生與高堂生同時;兩人所傅不同;故轉而言容禮。叙容禮畢;接以“而瑕丘萧奮以禮爲淮陽太守”;又轉而言《禮經》書本;二“而”字都是轉折之詞;用以界劃禮與容;非常分明。萧奮以後的事;司馬遷或不及知。末句“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是總結容禮。此“言禮”與文首“多言禮”同義;也是泛指古禮和秦、漢新儀;與“以禮”之禮内涵有廣狹之不同。洪氏既不注意前後禮字所指有異;又不區分禮與容之不同;遂有此誤。從上文辨析中可以看出;祗要撇開傅”容”一係;《史记》的叙述縱屬含溷;高堂生傳萧奮的事實還是顯而易見的。其實司馬遷述萧奮另行發端;不言從何人受學;也不過文情詭譎而已。
漢初朝廷輕視經學;以漢儀替代古禮;以致高堂生在民間講說《禮經》的事跡湮没不彰;所傅弟子見于记載的衹有蕭奮一人。《禮记》大題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這不僅確認高堂生爲《禮經》第一代大師;而尤關紧要的是落實了這五傳弟子中的一傳蕭奮。
五
今文《禮》傳授的第二階段是兩漢禮學的全盛時期。《漢書·儒林傳》云(本章引《漢書》之文較多;故祗標篇名;下同。):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魯閭丘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记》。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
后蒼字近君;東海剡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后蒼治齊《詩》;著有《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后氏傅》三十九卷;又治《禮》;著有《后氏曲臺记》九卷;二經都曾完成師法。所云“通《詩》、《禮》爲博士”;不知他是《詩》博士還是《禮》博士。《儒林傅》爲后蒼之傅列于《詩》類;其《禮》學傳授則附見于《禮》類《孟卿傳》中;所以有人認爲他是《詩》博士。可是;《傳·赞》述武帝所立今文經博士明记“《禮》后”;而齊《詩》“夏侯始昌最明”;又受武帝推重;尚且没有被立爲博士;怎會反而立其弟子;由此可證后蒼是《禮》》博士。
根據上引《孟卿傳》;很清楚地看出;在西漢今文《禮》的發展中;后蒼是個中心人物;祗要弄明白他從政、治學的活動;其他問题都迎刃而解了。后蒼的今文齊《詩》受自夏侯始昌而傳授給翼奉、蕭望之、匡衡;他的今文《禮》受自孟卿而傳授給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縱然他的生卒年不可知;活動的年代無明文可據;但可以從和他有交往的人物方面推算出來。
(一)夏侯始昌是后蒼的齊《詩》本師。《夏侯始昌傅》云:“自董仲舒、韓婴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韓婴在文帝時爲博士;輩分高于董仲舒;兩人論于武帝前在元朔二三年;以後無事跡可述;當死于仲舒前。仲舒生卒年亦無考;根據蘇輿《董子年表》的考證;董氏死于武帝元封二年至六年之間。此說可信;然後知夏侯始昌得武帝器重在太初以後。所稱昌邑王即哀王劉;《武五子傅》云:“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爲昌邑太傅自在天漢四年以後。又稱“年老以壽終”;假定七十左右;但死于何年仍難考實;不得不從他的親族中找旁證。一證之于其族子;《夏侯勝傳》云:“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生年無考;從始昌學亦不知在何年。又云:“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官。”不知何年遷太傅。今案:宣帝時任太傅者有丙吉、疏廣、黄霸、蕭望之等人;《本傳》俱有记載;還可以據以查核。《丙吉傳》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数月;遷御史大夫。”《疏廣傳》云:“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在位五歲;上疏乞骸骨;許之。”兩人相繼任太傅;疏廣離職在元康三年。《循吏傳》云:“天子以(黄)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後数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據下詔稱揚事知在神爵四年。《百官公卿表》不列太子太傅職;但于他官升遷往往有所涉及;于五鳳三年:“黄霸由太傅遷御史大夫。”于神爵三年:“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三年貶太子太傅。”黄霸于神爵四年任太傅;至五鳳三年離職;由蕭望之繼任。于黄龍元年:“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這是受宣帝遺詔輔政而改官的。根據傳、表所述核算;自地節三年至黄龍元年;太子太傅一職;祗有元康三年至神爵四年不知由何人擔任。《丙吉傳》又云:“制詔丞相;其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丙吉受封時夏侯勝任太傅;據《外戚恩澤侯表》“博陽定侯丙吉;元康三年二月封。”恰好正是這段時間。由此可證;夏侯勝于元康三年由長信少傅遷官;繼疏廣爲太子太傅;至神爵四年“卒官”;即由黄霸繼任。死時年九十;由神爵四年上推;當生于景帝中三年。據勝之生年推始昌生年;勝“少孤”而從族父受學;必在童年;至少少于始昌二十多歲;則始昌當生于文帝前十年以後。再證之于其族父;《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傅族子始昌。”張生從伏勝受《尚書》當在吕后時代;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始昌;兩世當歷四十年;始昌受《尚書》當在景帝中六年間;年二十左右;與上文推定生于文帝前十年以後適相吻合;年壽七十左右;當死于武帝天漢、太始之間;與上文推定任昌邑王太傅在天漢以後亦相吻合。推定始昌生于文帝前十年以後;年三十授經;則后蒼從始昌學齊《詩》當從武帝建元、元光間開始。
(二)孟卿是后蒼的《禮經》本師。《儒林傳》云:“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而《疏廣傳》云:“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后蒼與疏廣既是同郡;又是同學;年齡不會相差太大。又云:“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徙爲太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皇太子即元帝;《元帝紀》云: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然則年十二時在元康三年;疏廣以“年篤老”求去;當在七十以上;以此上推;當生于武帝建元之間。與孟卿同爲蘭陵人;云“少好學”;少年從師受《春秋》;當在武帝元狩、元鼎之間。后蒼從孟卿受《禮》;也不會早于此時;是從元狩、元鼎間開始的。
(三)萧望之是后蒼的齊《詩》弟子。據《蕭望之傳》;他于地節三年從諫大夫選充平原太守;以後歷少府、左馮翊、大鴻臚、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宣帝死時受进詔輔政;改前將軍、光祿勛。自少府以後;《百官公卿表》都有记載;升遷歷歷可考。初元二年;被弘恭、石顯誣陷;逼令自殺。臨死時云“吾嘗備位將相;年逾六十矣”;而前一年鄭明奏记;稱望之“至於耳順之年”;可證死時年六十一;據以上推;當生于武帝元封四年。生卒年既如此確鑿;自可根據他的受學時間來推定后蒼的授經時間。《本傳》云:“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 ;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阁曰不願見。”丙吉薦望之在誅上官桀後;誅上官桀在元鳳元年九月;次年被薦而焉霍光召見;算來此時年二十九歲。被薦之前;在太常爲博士弟子員和從白奇、夏侯勝問學;至少兩年;那末他從后蒼學齊《詩》的“十年”;當在武帝徵和元年至昭帝始元四年之間。
依據以上論證推定:后蒼從夏侯始昌受齊《詩》于武帝建元、元光間開始;從孟卿受《禮經》于元狩、元鼎間開始;蕭望之從后蒼受齊《詩》在武帝徵和元年至昭帝始元四年;這三點確定下來;后蒼的一生經歷自可約略考定。他于武帝初年從夏侯始昌受學;如果援蕭望之年十七受齊《詩》的例子作類比;其生年不會早于景帝中元年。從生年推定卒年;他到武帝末年已六十多歲;到昭帝末年已七十五六歲。據《霍光傳》載廢昌邑王贺奏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蒼議”;霸即《孔光傳》“霸昭帝末年爲博士”的孔霸;蒼即后蒼。事在昭帝元平元年六月;與《百官公卿表》“宣帝本始二年”下云“博士后蒼爲少府;一年遷”;《本傳》云“爲博士至少府”均合。后蒼從建元、元光間起受《詩》、《禮》兩經;經過若干年學成;徵和以後開始傅授弟子;即在此時立爲博士;一直到本始二年遷少府;少府遷官以後;就更無其它事跡可考。《宣帝紀》云:“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這次石渠閣會議由后蒼齊《詩》弟子蕭望之主持;又有《禮經》弟子聞人通漢、戴聖參加;會議討論涉及《禮經》;分歧很大;如果后蒼還健在;豈有不備顧問之理!可見他在本始二年由少府遷官;因病廢或死亡而未曾到職;所以各種记載都没有下文了。
《武帝紀》云:“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同。而《儒林傳·赞》則云:“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二說相矛盾。有人根據《贊》語;以《禮》后氏立博士在建元五年。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爲照上文的推比;后蒼從孟卿學《禮》從元狩、元鼎間開始;不可能在建元時被立爲博士。《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引《七略》云:“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记之曰《曲臺记》。”有人據此二文;以爲后《禮》立于宣帝;並以《贊》語爲誤。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因爲明明昭帝元平元年廢昌邑王賀奏有“博士蒼”的记載;其時昭帝已死;宣帝未立;而昭帝一代又没有立過任何博士;后《禮》不可能立于宣帝之世;《贊》語固屬含糊;武帝末年已立后《禮》則無可疑。其實;各種记載雖有不確切處;但都不是憑空臆造。武帝在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在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都是從制度上確立經學獨尊的局面;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但事屬草創;不可能-時《五經)俱立。文、景時代曾在太常立過博士的三家《詩》也不見得同時有適當的大師招之即來;何況從未立學的《禮經》;遴選博士決非易事;遷延至武帝末年方得立于學官是完全可能的。后蒼至本始二年以後尚健在;說宣帝世禮學他爲“最明”是對的;但不是此時其學初成的意思;《曲臺记》九篇“說《禮》數萬言”;未必全屬《射禮》解說;平時有所輯撰;因從事習射;完成其書;如服虔所謂“在曲臺校書著记;因以爲名”;也不是至此時始完成師法的意思;因此二者都不能作后蒼在宣帝時立爲博士的證據。各書记載縱有不一致處;加以疏解;並非絕不可通。這樣說來;后蒼的生卒年及其一生經歷;雖没有係統詳備的记載;經過反覆推比;大致可以弄清楚;如上文所論述。
論定后蒼從孟卿受《禮經》在武帝元狩、元鼎間;于是;孟卿從蕭奮學;蕭奮從高堂生學;其時间亦可據以推定。高堂生經歷秦火;惠帝除挾書律後;匯輯、寫定《禮經》十七篇;其傳授弟子;當在吕后、文帝時代。蕭奮傳孟卿;當在景帝中元年以後。這些學者;不過講誦經文;没有撰作记傳;師法未備;不僅在文、景立《詩》、《春秋》博士時;不能與申公、胡毋生等人相頡頏;就是到武帝置《五經》博土時;也没有具備人選的條件;以致《禮》博士一直空着;到武帝末年后蒼學成;今文《禮》才得立于學官。
后蒼所授齊《詩》弟子和《禮經》弟子應有區别;前者是私人傳授;《蕭望之傳》可證;後者才是太常的博土弟子員。其中知名的有四人;都是在武帝後元到宣帝本始這十七、八年中先後在太常從后蒼受學的。《儒林傳》云:
孝公(慶普)爲東平太傅。(戴)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
四弟子的事跡已無法詳考。闻人通漢和戴勝曾參加過甘露三年召開的石曲閣會議;可惜當時编定的《石渠議奏》關于《書》、《禮》、《春秋》、《論語》、《孝經》共一百五十五篇已經散佚;遺留下來的衹是一些討論《喪服》的殘文。就這些殘文而論;闻人通漢的見解頗爲精深;可信在四弟子中最爲傑出;但偏偏他没有建立家法;始終被排擠出官學之外。其原因可能由于石渠閣會議討論《喪服》時他堅持“大宗可絕”;遭到很多人反對;這一主張;不僅違反師法;違反本經;而且政治上直接動摇宗法制度的根本問題;官學是不能容忍的。他居四弟子之首;顯然年齡最大;從學最早;但既未繼立爲博士;又未傅授弟子;對今文《禮》的發展貢獻不大;後人就不再多加論列。
大、小戴、慶氏分爲三家;歷代學者深信不疑;其實當時立于學官的過程非常複雜;《漢書》有關各篇的记述自相矛盾;非查明底蘊;不應輕作判斷。《藝文志》云:
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後漢書·儒林列傅》述前書云:“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但三家怎樣完成家法;何時立爲博士;則隻字不提;史家所述太不明確;斷難信據。《儒林傳·赞》云:
至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
據此則慶氏《禮》在西漢並未立於學官;與前文不同;再根據上引《儒林傳》之文;則戴德亦未曾擔任過博士;與此文又異。衹有戴聖立于學官;志、傳吻合;似屬可信;但所謂“孝宣世復立”和“以博士論石渠”;同《何武傅》所述;在時間上又對不起頭來。因此這千載懸案;衹有盡可能把他們的經歷一一疏通;方有解決的可能。戴德擔任過“信都太傅”;元帝以後有二信都王:(一)中山孝王興;于元帝建昭二年初封信都王;至成帝陽朔二年徙封爲中山王;(二)楚孝王囂之孫景;于成帝绥和元年立爲定陶王;哀帝建平二年徙爲信都王;其事俱見《宣元六王傳》和《諸侯王年表》。戴德所傅;從年齡上約略估計;當屬前者。《通典·禮》、《禮记》孔疏引戴德《喪服變除》(又名《喪服记》)殘文十餘條;都是排比經文;絕少勝義;恐難據以别起家法。此書不知撰于何時;與“善說禮服”的蕭望之應該頗多淵源(蕭望之的《禮服》之學受於夏侯勝);但没有被引爲同調;看來不像在宣帝時所作;據此可證他治學從政主要在元、成之世。《後漢書》以戴聖爲戴德的兄子;叔侄齊名;年齡相差不大。《何武傳》云:“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日:‘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毁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盗;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其事在何年?據《百官公卿表》于成帝河平三年下:“传中中郎將王音爲太僕;三年遷。”又于陽朔二年下:“传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可據以推定;何武遷揚州刺史;戴聖免九江太守;都在陽朔二年以後。《何武傳》又云:“(宣帝)神爵、五鳳之間;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復眾等共習歌之。”五鳳元年何武年十五;至陽朔二年已五十歲;而戴聖斥爲後進生;則他自己當在七十以上。以此上推;當生于武帝天漢、太始間;到昭帝末年不過二十三四歲;“年十八以上補博士弟子”;他詣太常從后蒼學《禮》當在昭、宣之間。二戴同事一師;戴德縱使受業較早;亦必在昭帝之世。《儒林傳》說聖先爲博土;後“至九江太守”;而《何武傳》則說聖先任太守“自免;後爲博上”;《漢書》二傅自相矛盾。據《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小戴《禮》不可能在甘露以前别起家法;立于學官;甘露三年之詔與《儒林傅·赞》所述是同一事件;而詔書上没有提及大、小戴《禮》博士的事;是不是记述疏漏;應在其他记載裏求取證明。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非但與《宣帝紀》完全相同;可互證其可靠;而且劉歆爲爭立古文經而責讓太常博士;其述前代所立博士;豈容有絲毫差忒。還有一點應特别注意;宣帝所立;大、小夏侯之于歐陽;梁丘之于施、孟;穀梁之于公羊;都屬與已立之學“相反”而“並置”。戴德、戴聖此時尚在初學;不可能别起家法;與后蒼師弟相承;義無相反;同此次立學宗旨不符。據此数端;知大、小戴《禮》都不是甘露三年所立;《傳·赞》之語;界線不明。王國維氏以爲戴聖“實爲后氏《禮》博士;尚未自名其家”;似亦有見及此而爲此說。但他如能一讀《何武傳》;就會明瞭彼文依事詳述;層次分明;與《儒林傳》所說“以博士論石渠”一樣的確鑿可靠;則論證將更爲完備。這樣說來;戴聖與公孫弘在武帝建元中、師丹在元、成之際先後兩度擔任博土一樣;他在甘露中以其師后蒼師法立爲博士;至陽朔二年以後;别起小戴《禮》師法;復爲博土。《漢書》叙事疏略;故有此失。
大戴《禮》怎樣别起家法;還得聯繫二戴弟子的經歷和學術成就全面考察。《儒林傅》又云:
(慶)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游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傅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關於慶普及其弟子的所謂“慶氏《禮》”;放在下文一起評述。在這裏主要探討二戴用何種解說來别起家法。戴德撰有《喪服變除》;戴聖在石渠阅會議上發表過自己對《禮經》的見解;這些雖可算是《禮經》解說;但前者不及全經;後者恐未必成;作爲家法的依據是不够的。除此以外;兩人都曾選輯古“记”;《禮记》大題孔疏引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记》八十五篇;戴聖傳《记》四十九篇。”此說不見于《漢書》;而《後漢書·橋玄傅》云:“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记章句》四十九篇;號橋君學。”橋仁繼承其師之學;爲《禮记》作章句;則二戴選輯古“记”之說是可信的。慶普撰述不詳;其後學曹褒亦“又傳《禮记》四十九篇”《後漢書·曹褒傳》)。可見三家都以選輯古“记”作解說《禮經》的著作文式。大戴弟子徐良爲博士;雖不知曾否研討古记;但可以推定;他也是繼承其師之學而立爲博士的。戴德生前未任博士;其弟子徐良爲博士;與孟氏《易》“上(宣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至其弟子白光、翟牧;“皆爲博士”;正好類比。《百官公卿表》于孝平元始二年下:“大鸿臚橋仁”;又于五年下:“大鸿臚左咸”;則橋仁任大鸿臚在元始二年至四年。徐良與橋仁同行輩;他任博士在何年;雖不可知;總不出哀、平之際。這樣說來;西漢確曾立過大、小戴《禮》;《儒林傅》所述並非全屬子虚;不過傅闻失實;《傳·赞》誤繫于宣帝之世。
徐良、橋仁、楊榮之後無傅人可考。《後漢書·儒林列傳》述前書;連徐、橋、楊三人都没有提及;可見今文《禮》至徐良一代已成“絕學”;再也没有什麼發展的了。
六
兩漢禮學傳授的第三階段是慶氏《禮》的興起。慶氏學以修訂漢儀爲内容;本來不應屬于今文《禮》範畴。但是它的首創經師慶普是后蒼的弟子。向被當作后《禮》分爲三家的一家;同時;“習慶氏《禮》”的學者也曾學習過《禮經》;議論漢儀時往往掺雜一點古禮作緣飾;因此歷代禮家含糊地没有把他們排除在今文《禮》傳授之外。我們論述禮學的發展;固然要承認兩者易于混淆的事實;但更爲重要的是必須明辨其真相;使人們了解慶氏後學所推行的東漢重修漢儀;仍然以秦儀爲藍本;與十七篇古禮的性質完全不同;應該嚴加分别。
慶普事跡無考。他擔任過“東平太傅”;《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奸犯法;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慶普可能就在此時任太傅;因連坐而仕進受挫折;以致後來不甚顯名。《漢書·藝文志》云“三家立於學官”;但無其他记載證明其曾任博士。東漢初年盛行慶氏《禮》;對其學内容;史家絕少记載;禮家亦懵然無所知;以後代傳人之學來窥測其本師之所爲;然後知慶普實是從事漢禮儀的學者。
東漢禮學衰微;《後漢書·儒林列傳》禮類衹列慶氏《禮》學者董鈞一人;其傅云: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年七十餘;卒於家。
董鈞從王臨學慶氏《禮》;而王臨其人則無從稽考。《漢書》有兩王臨;一爲王莽子統義陽繆王;一爲平昌釐侯。前者顯非傳經之士;而後者曾從翼奉受學;還擔任過太常卿;頗似經師。然據《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云:“(元帝)永光三年;釐侯臨嗣;二十一年薨。”死于成帝鴻嘉元年;而董鈞死于明帝永平中;年七十餘;上推當生于成帝鸿嘉、永始之間;無從學可能。《漢書·百官公卿表》于孝成建始四年下:“河南太守漢爲大鴻臚;一年免。”于河平四年下:“大夫韋安世爲大鴻臚。”其間缺自河平元年至三年行此職者一人;可見史有阙文。上文論證;戴聖任博士在陽朔以後;年已七十餘;戴德從政、治學在元、成之世;慶普任東平太傅在宣、元之際;三者互證;可信慶普傳授弟子在元帝永光、建昭之間;這史書失載的王臨;當與夏侯敬、慶咸同時受業。陳延傑《經學概論》所附《士禮傳授表》把三人同列爲慶普弟子;雖無任何說明;看來也出于同樣的考虑。
董鈞以“習慶氏《禮》”而參與明帝時草創五郊、宗廟的祭祀禮儀;他的參議;又“多見從用”;顯然不屬于《禮經》十七篇的内容。
同時習慶氏《禮》的還有曹充;《後漢書·曹褒傳》附見其父事跡云:
書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拜充传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受詔議禮儀事在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完成禮制在明帝永平二年;前後五年;即《後漢書·禮儀志上》所云“於是七郊禮三雍之義備矣”。重修漢儀;早在建武十九年就由張純提出來的。他認爲“舊章多闕”而“宗廟未定;昭穆失序”;需要依據“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來恢復西漢禮制。到永平定禮儀;雖仍由張純主持;而董鈞、曹充的參議;起了決定作用。曹充主張“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當然不會考虑到古經與古“记”應如何繼承;所以董鈞的“習慶氏《禮》”;曹充的“持慶氏《禮》”;其實都是表明異于后、戴之《禮》的意思;歷代禮家忽視這一點;還以爲慶普不過是后氏係統的一個家法;真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到章帝、和帝時代;又有曹褒繼承慶氏之學;《曹褒傳》又云:
褒傅充業;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畫夜研精。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传中;從駕南巡。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记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十簡;其年十二月奏上。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黼、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寝其奏而漢禮遂不行。有頃;徵再遷;復爲传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记》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曹褒“慕叔孫通漢禮儀”;所定天子至庶人冠、婚、吉(祭祀)、凶(喪葬)制度一百五十篇是取得叔孫通二十篇《漢禮儀》原本之後撰作的;顯然這是爲漢朝廷制定的“新禮”;不見得對《禮經》十七篇有所參考;而《通議》十二篇;更無疑是對《漢禮儀》的逐條闡發;他完全繼承了叔孫通的遗法。
根據上引諸文;可以說明三個至爲重要的問題:第一;三人中祗有曹褒明確提及“慕叔孫通漢禮儀”;而事實並不如此;在前;曹充已提出過“三王不相襲禮;”;與叔孫通所主張的“三王不同禮”;都是引伸《禮记·樂记》之義來否定古禮;而董鈞參議的五郊、宗廟祭祀;又何嘗不是惠帝命叔孫通“定宗廟儀法”的重複;可見三人是一脈相傳的;都是叔孫通定漢儀的繼承者。他們都不是今文《禮》的學者。
第二,曹充“作章句辯難”之後;“於是遂有慶氏學”;曹褒“撰次百五十篇”、“作《通儀》十二篇”之後;“慶氏學遂行於世”;那末所謂東漢盛行慶氏《禮》;它的内容應該包括:甲、曹充的定封禪禮;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乙、曹褒的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而董鈞所參議而“多見從用”的草創五郊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也應屬于甲項。丙、曹褒撰作《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记》四十九篇;前者可能援引《禮經》的一些威儀章服作緣飾;後者顯然從小戴所輯《禮记》中擷取郊天社地明堂月令養老等禮的殘文剩義;作自己創制新禮的依據。這些;與《禮經》十七篇、《禮记》述禮諸篇是没有多大關係的。上文說過;二戴用選輯古“记”來替代經義解說;畢竟還是緊密配合十七篇經文;以傳經爲主要任務。而慶普的禮學;從東漢慶氏後學奉行師說來看;也無非上述三個方面的内容;與其師后蒼和同門闻人通漢、戴德、戴聖大相徑庭;事實上也屬于叔孫通一流人物。這樣說來;不僅董鈞三人;而且連慶普在内;都不是今文《禮》經師
第三,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議論建置的封禪、七郊(或五郊)、三雍等禮;就是秦始皇、漢文帝、武帝所要實行的祀典。撇開方土怪誕之說;秦始皇實行封泰山、禪梁父;衹是“其禮頗探太況之祀雍上帝所用”;漢文帝祗是“始郊見雍五疇祠;衣皆上赤”;“以郊見渭陽五帝”;在長安門“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武帝衹是“(郊)天地牲角璽栗”;祠后土“於澤中国丘爲五壇;增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黄”(以上引文並見《史记·封禪書》)。這些都是史況之官草擬的;而史祝都是秦故祝官及其後代。叔孫通創制漢禮儀是“皆因秦故”;可見名爲漢禮實是秦儀。而東漢再受命制禮以示百世;不過是西漢所創新禮的恢復;而董鈞、曹充的“參議”;更不過是一些祀典中的“禮儀”、“威儀章服”;曹褒的“撰次”;顯然衹是叔孫通《漢禮儀》的抄襲和輯錄。總起來說;東漢重修的禮儀;事實上仍然是秦儀的復現。這種秦儀當時稱之爲“慶氏學”;那末慶氏《禮》的内容也就是秦儀的參酌而已。《漢書·禮樂志》載劉向上議云:“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秦儀與齊、魯儒生所傳《禮經》在儀式上是不一樣的;在制度原則上說是對立的。慶普雖是后蒼弟子;他的禮學與其師完全相反;從經學立場看;他在生前不能取得傳經之士的擁護;以致湮没無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從上面三個問題的分析中;揭示了慶氏《禮》的真相;分清了慶普與大、小戴在禮學上的本質差别;從而使歷代學者對兩漢禮學的模糊認識得到了澄清。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漢書》记載三家博士存在志、傅自相矛盾的問題;才有可能獲得解決。《儒林傅·赞》所說“立大、小戴《禮》”;上文已核定證實;《藝文志》所說“三家立於學官”;還没有落實。對待這個問題;需要從解決《後漢書》存在同樣的問題人手。《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颜;凡十四博士。”《續漢書·百官志》、《漢官儀》同;都說光武帝立十四博士中衹有大、小戴《禮》;而董鈞三人的傳裹又都說“習慶氏《禮》”而被拜爲博士;也是自相矛盾的。王國維氏《漢魏博士考》(《觀堂集林》卷四)云:“案後漢初曾置慶氏《禮》;當時爲《禮》博士者;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鉤;皆傳慶氏《禮》者也。傳二戴《禮》而爲博士者史反無聞。疑當時《禮》有慶、大、小戴三氏;故班氏《藝文志》謂《禮》三家皆立于學官;蓋誤以後漢之制本于前漢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至後漢末《禮》博士衹有大、小戴二家;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耳。”果如王氏所論;則東漢初應有十五博士;其考證失于周密;不足憑信。其實問題的鬧鍵在于:太常所拜是不是全部經學博士;董鈞三人是不是《禮經》博士?在辨明慶氏《禮》真相之後;從博士官制度上考察;這些問題是不難作出正確答案。在西漢;《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黄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太常職掌朝廷實行的禮儀;而要有通曉古今禮制的學者擔任顧問;所屬博士在漢初的職掌是“通古今”;備皇帝諮詢;都是熟習傳记百家語的人物;當時稱爲傳记博士;其中也包括與本職關傺密切的漢儀博士;叔孫通任博士草擬朝儀;即是顯例。武帝能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其職掌改爲教授弟子。但百家廢而太常禮儀不廢;這種漢儀博士是否保留雖無明文可據;但《漢書》諸列傳裏曾记載些不明治何專經的博士;如《薛宣傅》“博士申咸給事中;毁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兩龔傅》“博士夏侯常(與)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常復謂(龔)勝:禮有變”;兩人所言;都涉及當時所行喪祭禮制。又《北堂書鈔》六十七引司馬彪續漢書》云:“魯充爲博士;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則完全是漢儀。無疑這些都是太常的漢儀博士。到東漢時;《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常卿一人;本注日: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本注日:“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完全承襲武帝以後的制度。太常的職掌;首要是“奏其禮儀”;非但不屬于《易》、《書》、《詩》、《春秋》博土的專業;即使《禮經》博土也不見得在行;因此在他“選試博士能否”中必然包括漢儀博士;才能執行其任務。董鈞三人“習慶氏《禮》”而熟習漢代新儀;彼等被“徵拜博士”;無疑像叔孫通那樣;擔任了太常的漢儀博士而不是《五經》的《禮》博士;所以東漢《五經》十四博士中没有慶氏。“習慶氏《禮》”的董鈞三人既屬太常漢儀博士;那末慶普本人如果曾任博士的話;不可能不是這種漢儀博士;這是不言自明的。班固、范曄等分辨不清漢代禮學同時並存齊、魯所傅《禮經》和當時創制“漢儀”兩個部分;又不明白今文官學不應容納漢儀博士;在他們的書裏作了含糊籠統、自相矛盾的记述;以致懸疑千載;一直得不到解決。其實衹要辨别兩種禮制的對立;這個疑案就涣然冰釋了。
東漢十四博土中雖有大、小戴《禮》;但無一傳人可考。《後漢書·儒林列傅》云:“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就是說東漢官學一直有二戴博士教授弟子員的;不過博士或博士弟子員都把它當作仕進的階梯;在經學上没有成就可言;因而没有傑出的經師可记述。東漢初年盛行慶氏《禮》;但從褒以後也没有傳人可考。當然;每年舉行各種禮典;太常漢儀博上的議禮文章照例要寫的;不過和帝以後禮儀方面也没有重大的興革。看來;不但今文《禮》日益衰落;漢儀也僅僅虚應故事而已。
最後需要附帶提一下的;《後漢書·董鈞傳》云:“中興;鄭策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傅《禮记》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據《後漢書·鄭玄傳》云“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记》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如果這樣標點無誤;《三禮》受自張恭祖;但不知張氏是否小戴《禮》博士?黄以周氏據《董鈞傳》以爲“所云小戴《禮》即十七篇也”。又云:“漢初傅今文十七篇者;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其本各異;當時别其家法;又稱曰大戴《禮》、小戴《禮》。”(《禮書通故》第一)。此云“小戴《禮》”與《何武傳》所稱“《禮經》號小戴者也”同意;都是后蒼弟子二戴各立家法的名稱。師法、家法都是指他們對經文的解說。家法之不同取决于解說經文之義的不同而不在經本文字之有異。固然;所持經本的文字不同會引起解說的不同;但不等于說解說不同都是經本文字不同所引起的。黄氏没有提出任何證據;僅僅以“别其家法”來證明“其本各異”;實屬武斷。鄭玄《三禮目錄》詳列大、小戴编排篇目次第的不同;其注《禮經》;又把今古文二本以及二本或作的不同文字;甚至不屬于今古文的異字;一一叠之于注。如果“本習小戴《禮》”而小戴所持之本文字“各異”;他豈會不把這些異文收人注内?根據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我們判断戴德、戴聖所據經本都是后蒼所傅之本;文字並無異同。戴是以輯錄古“记”替代解說來建立家法的;二家所輯不同;導致對十四個禮典和一篇《喪服》(即《禮經》十七篇)構成係統的認識就不一樣;因而在篇目次第的编排上也不一致;這倒表現了他們“别其家法”的意思。至於此傅所云;不過說鄭玄早年受學時;《禮經》受小戴家法;因而他後來又爲小戴所輯《禮记》四十九篇作注。到他學成之後;對今古文無所軒輊;對本無傳人的古文《禮》尚且探錄;大、小戴编次上的不同當然不足介意;注《禮經》又改從劉向《别錄》编次;完全擺脱今文小戴家法的羈絆了。因此;我們論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没有必要把鄭玄列人今文學係統;只要附帶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七
根據以上的考證;编制了《兩漢今文《禮》經師傳授年代表》。對今文《禮》經師的傳授;前人的考證是很疏略的。而我們探討的結果;也幾乎没有一個經師考得出確切的生卒年。但依據各種记載作了嚴密的推比後;取得上述八世經師的大致年代;雖都是約数;但可以相信不致有大的偏差。事實上看了此表;對兩漢今文《禮》的傳授也已瞭然。

今文《禮》在西漢祗有六傳;延續到東漢初年;其最後兩世師承上雖紧屬于今文《禮》方面;實際上都是漢儀學者。所謂“后蒼最明”;就是后蒼以前没有立于學官;而后蒼也祗有编撰了《曲臺记》之後;才得完成師法;故立學已在武帝末年。后氏弟子聞人通漢、戴德、戴聖學有成就;但立爲博士的衹有戴聖一人;二戴弟子中祗有徐良用其師大戴的名義立過博士;這就是所謂西漢“立大、小戴《禮》”。慶普雖名隸后蒼弟子;現在通過東漢“慶氏學”的研討;查明他是從事修訂漢禮儀的學者;可能曾在太常擔任過漢儀博士;事實上已不是今文《禮》經師了。過去禮家侈談慶氏《禮》盛行于東漢初年;現在查明董鉤三人都是參與重修漢儀的學者;不是今文《禮》的傳授者。東漢官學設有今文《禮》一席;還立了大、小戴兩個家法;但無傳人可考;《禮經》在東漢經學史上是個空白點。總起來說;今文《禮》在兩漢並不興旺;與《詩》之有魯、齊、韓三家;《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易》之有施、孟、梁丘、京房四家;《公羊》之有嚴、顏兩家;那樣的師法、家法完備;弟子傳授不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原載巴蜀書社《顧頡剛先生九秩誕辰學術論文集》)
上一篇 : 略倫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
下一篇:领导关怀 名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