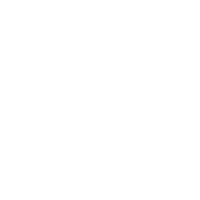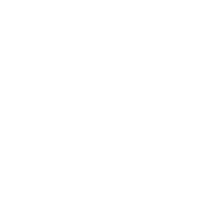略倫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
 发布日期:2023-06-14
发布日期:2023-06-14  浏览量:54
浏览量:54
沈文倬
一
“禮”;除了如“周禮所以本也”(《左傳》閔公元年)等語被當作政刑法度的大名以外;絕大部分指奴隸主贵族經當舉行的各種禮典。春秋前期;一些博通古今、頗負時譽的人物;對正在實行的禮典;都曾加以議論;一致强調禮對政治的主導作用。例如:周惠王、襄王時代熟于古史的内史過曾經說過:“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左傳》僖公十一年);晉哀侯的大夫師服說:“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左傳》桓公二年);衛文公的正卿寧莊子說:“夫禮;國之紀也;國無紀不可以終”《國語·晉語》);晉平公、昭公時代以博識多闻著稱的叔向也說:“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這些言論出現在孔子以前;而且都以引爲鑒戒的語氣來論述;可見周代奴隸主階級早已認識到禮的政治作用;說禮樂出于儒家顯與事實不符。當然;孔子及其後學是繼承和發展了這個傳統;在社會性質已開始變革、古禮已漸被抛棄的時候;他們還企國挽回頹勢;積極鼓吹。孔子曾明確地提出“爲國以禮”(《論語·先進》)的主張;而他的後學;在《禮记》的《祭統》裏說“治人之道;莫急於禮”;在《禮運》裹說“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直到戰國末年;荀況還堅持“爲政不以禮;政不行也”(《荀子·大略》);“禮者;治辨之極也”(《荀子·議兵》);幾乎一脈相承地把禮當作推動政治的重要工具。
“禮以體政”;適應于政治需要的各種禮典是具體的。《尚書·堯典》所云“有能典朕三禮”(鄭玄注:“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禮记·祭統》所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指吉、凶、賓、軍、嘉五大類的禮典);按門類來說是三禮、五禮。《禮记·昏義》云:“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大戴禮记·本命》云:“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军旅;此之謂九禮也。”《禮记·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嘗、禘之禮;饋、奠之禮;射、鄉之禮;食、饗之禮。”分列通行的禮典就是八禮、九禮、十禮。奴隸主贵族舉行各種禮典是他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准此而論;上面所述議論“禮”的一般意義;都是從具體的禮典;如内史過從錫命禮、叔向從會禮、師服從世子命名禮中概括出來的;其實即使抽象到訓詁上用“履也”來解釋“禮”字;仍然是指在禮典中儀式的實踐。
因此;考查古代“禮”的發展;首先要弄清楚各種禮典是怎樣演習和實行的;然後進一步探索流傳下來的《儀禮》書本是怎樣撰作的。對于這一點;過去不少的學者忽略了;甚至把它颠倒了。
舉行禮典;要求儀式無所差忒;因而貴族們很注重禮儀的演習;習禮成爲贵族教育的重要部分。官學裏禮典演習是一門主要的課程。《禮记·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作、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制》篇應屬秦、漢間人論述前代爵禄、學校、選舉、養老等制度的作品;近人考定《周易》晚出;而“六經”之稱起于晚周(初見于《莊子·天運》;又見于《禮记·經解》);那末這一反映春秋以前官學教育贵族子弟只有詩、書、禮、樂四個科目的记載;燼管出于後人的傳說;還是可以據爲實錄的。再證以《史记·孔子世家》所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子在官學所受和以後在私學所教;還只四個科目;可信前說決非誣妄。
四個教學科目中;《詩》、《書》和“禮”、“樂”是不一樣的。《詩》、《書》是學習文字记錄的書本;而“禮”所學習的是當時實行各種禮典的具體儀式。《論語·述而》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謂雅言?《荀子·榮辱》云:“摩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儒效》又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文;雅通夏;顯示地域習俗的差異。在語言上;夏言就是與越言、楚言相區别的中原地區華夏音讀。華夏音被當作標準的雅音或正音;故鄭玄注云“正言其音”。何謂執禮?《禮记·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執禮者詔之。”演習禮典儀式要按赞禮者宣唱行事。孔子教弟子;誦讀《詩》《書》書本用夏言;擔任赞禮宣唱也用夏言。同是學習;前者是誦讀文字而後者是演習儀式;故鄭玄注云“禮不誦;故言執”。没有提到“樂”;樂指以七音配十二律來使用各種樂器;不在夏言誦讀之列。音樂演奏以“詩”爲樂章;詩、樂結合便成爲各種禮典的組成部分。邵懿辰說:“樂本無經也;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禮經通論》)論證樂無書本;邵說確不可易。但從禮、詩、樂三者的相互關係上看;舉行禮典需要詩、樂組成的音樂配合;那末在教學上也應以禮典演習爲主體;三個科目中學詩、學樂是從屬于學禮的。
各種禮典是怎樣實行的?依據本文所應涉及的範圍;没有必要從遠古的傅說裏追索所謂“禮起于俗”的起源問題;主要探討它在社會進人劃分階級以後的發展進程。在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社會裏;統治階級爲了貫徹其階級意志、推行其政治設施來確保它所統治的社會的正當秩序;需要建立一些制度规程。在古代歷史上;很大一部分制度规程就是“禮”。具體地說;就是根據政教、外事、兵戎、震耕、狩獵、宗族、文化等方面的實際需要;逐漸形成各個門類如朝覲、盟會、錫命、军旅、祭禱、藉蜡、喪葬、搜阅、射御、聘問、賓客、學校、選舉、婚配、冠笄等禮典。禮不是超現實的東西;無論哪種禮典;其具體儀式都是從統治階級的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只不過被加以装璜和粉飾;成爲一幕幕莊嚴肅穆、令人敬畏的場面而已。
在殷周時代;奴隸主贵族在政治上、思想上是依靠和運用天命思想來建立和鞏固它的統治的。天命思想是奴隸制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尚書·盤庚下》:“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尚書·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墨子·非命下》引佚《書》:“不慎厥德;天命焉葆。”《大盂鼎》:“丕顯坟王;受天有大令(命)”(《兩周金文辭大係》錄编18)。《詩·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就是說;奴隸主贵族的大小等級是依據天帝所賦予的德性來確立的。命是天授的;因而天帝所命定的等級是不容僭越的。而這種不容僭越的等級身份;要用“禮”來表現;這樣;“禮”和天命思想就直接聯紧起來了。具有何種等級就用何種禮典:有的禮典只有某一級贵族舉行;比如覲禮只有王才能舉行;有的禮典各級贵族都能舉行而儀式不同;比如射禮;諸侯舉行“大射”;而卿大夫在鄉、州一級政權機構裏舉行的是“鄉射”;又如婚、喪之禮;自天子至庶人都能舉行;而在器物、儀式上加以區别;但又允許“攝盛”。每一禮典舉行時;参加者各按其等級身份使用着不同的器物(或同一器物而加以不同的装飾);同時表演着與等級相適應的儀容動作。差别顿爲森嚴;絰毫不容差忒;差忒了;不但要給予“非禮”的譴責;而且要被視作僭越、犯上、篡奪而加以罪戾。《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劉康公的話:“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就是這個意思。等級差别是唯一重要的。然而;只有人們自覺地遵守這種差别;才有利于統治階級內部各個等級在對天命的堅定信仰中組織起來;才能促使這種差别趨于鞏固。在實行差等分明的“禮”時;還需要用“樂”來進行協調;即所謂“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记·樂记》)。因此;各種禮典的實行都離不開樂的配合;樂從屬于禮而起着積極的作用。得到樂的配合;才能使森鼹的禮達到“禮之用;和爲贵”(《論語·學而》);“樂文同則上下和矣”(《禮记·樂记》)。它既表現了天命的不可侵犯性;又表現了上下安于天命的和諧性。
“ 禮不下庶人”(《禮记·曲禮上》);“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荀子·富國》);表現等級不可逾越而又上下安于這種等級的禮典;固然只在統治階級内部舉行;然而它真正的作用是:使人們從舉行各種禮典中;形象地感覺到這個责賤尊卑的等級差别出于天帝的安排;從而迫使被統治階級不得干犯而必須服從于他們的壓榨。因此;禮是推行階級統治的工具;這就是所謂“政之輿也”吧!
用禮來表現大小奴隸主贵族的等級身份;就各種禮典的内容來說;不外有兩個方面:其一;禮家稱之爲“名物度數”;就是將等級差别見之于舉行禮典時所使用的宫室、衣服、器皿及其装飾上;從其大小、多寡、高下、華素上顯示其尊卑贵賤。我們把這種體現差别的器物統稱之爲“禮物”。其二;禮家稱之爲“揖讓周旋”;就是將等級差别見之于參加者按其爵位在禮典進行中使用着禮物的儀容動作上;從他們所應遵守的進退、登降、坐興、俯仰上顯示其尊卑贵賤。我們把這些稱之爲“禮儀”。無論禮物或禮儀;都起着使等級身份凛然不可侵犯的作用;維護了奴隸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在他們看來;這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不容許任何人破壤和違反。在發展中;爲適應出現新的變化而由“知禮”的師長作部分的增加或削减。但在確定等級原則方面;社會性質没有起根本變革;它是不會有巨大 改變的。《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在夏、殷字逗;從漢人讀;見《漢書·杜周傅》杜欽對策引)就是明證。這樣說來;殷、周奴隸制社會所舉行各種門類的禮典;本是奴隸主贵族等級差别的體現;是他們的現實生活的集中反映;它決不是某一個人憑空的創造;因而它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從簡單向複雜;逐漸擴充和完善起來的。禮典由禮物和禮儀所構成;從贵族們現實生活中升華出來。奴隸主贵族每個成員從小就必须學習;成人後又長期實行;並以此爲異乎奴隸和其他平民的高贵的文化素養。所以;禮典的實踐先于文字记錄而存在;事實上當初用文字來记錄的客觀條件也不具備;因爲用竹木簡作爲書寫材料;至戰國時才較普遍。
用文字记錄下來的各種禮典;我們稱之爲“禮書”;是记錄“禮物”、“禮儀”和它所表達的禮意的文字書本;現存的《儀禮》十七篇就是它的殘存部分。說殘存;是根據現存十七篇經记本文來作出判斷的。《土冠禮·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公侯之有冠禮也”;當時有《公冠禮》《大夫昏禮》;今已佚。《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餐”;又记“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食即《公食》;今存;《饗禮》;今佚。可見有若干篇禮典的書本是在秦火中亡佚了。因此;我們認爲《儀禮》十七篇僅屬殘存;此外還有已佚若干篇。禮作出于後人的追记;可能對禮典在發展中出現的分歧作過某些整齊劃一的修訂;但主要的内容是不會有大差異的。但是;必須指出;禮書與禮物、禮儀不能等同;不是一個東西;歷代經學家侈談周公制禮作樂;便把《儀禮》說成是周公所作;是西周初年的作品;無疑是錯誤的。後來;歷史考古學者用西周彝銘來對照;發現它在文體、語詞上不像是西周的文字;而所述名物與出土實物相比較;也不盡符合;從而考定它的撰作時代當在春秋、戰國之間;這是可取的。但是他們把書中所记述各種禮典的内容也說成是春秋、戰國間某一諸侯國的實制;以前根本不存在這些禮典;我們認爲這也是片面的。之所以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頗之說;是由于把禮典和禮書看作一個東西了。如果認識到有了事實才有可能對事實進行记錄;上文所論證的由禮物、禮儀構成的各種禮典早已存在于殷和西周時代;而“禮書”則撰作于春秋之後;就没有君麼可以懷疑的了。
二
如上所述:禮典的實踐先于文字记錄而存在;自殷至西周各種禮典次第實行;而禮甚至春秋以後開始撰作。由于這種主張與歷代經學家和近代歷史考古學者的說法有很大不一致處; 其能否成立;還而要經過各方面的驗證核實。進行驗證時應該注意到:一、和任何事物一樣;“禮”也是從簡單向複雜、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禮家稱“殷質周文”;最初的禮典肯定不會有後來皆本所记裁的繁文縟節;因此某些歷史记載提到某一禮典時;固然由于簡略敘述而言之未詳;但也可能是當時的儀式原來就比較簡單。如果因爲记載未具後世規模而無視其存在;顯然是不對的。二、上文已證明十七篇僅屬殘存;一部分禮典魯本已在秦火中亡佚;因此不應該以現存十七篇的範圍來看待殷、周禮典。
殷代的禮典缺乏直接可资證明的记錄。在甲骨卜辭裏有名目繁多的祭名;五禮中只有吉禮尚可據以有所考證。爲祭祀貞卜俱屬卜定祭曰和祭法;它本身就是各種祭禮的第一個節目;因此;卜辭除了记錄祭祀、祭法的名稱外;很少反映祀典的性質和内容。早在1915年;羅振玉氏匯輯過二十多個祭名;但絕大部分“其義未詳”(見《殷虚書契考釋》)。以後;陳夢家氏曾用七個類目來區分三十七個祭名;除了“祈告之祭”、“合祭”兩類使人稍有認識外;其他如“以所薦祭之物焉名者”、“以所祭之法焉名者”、“特殊之祭”等;仍然無法增進對祀典意義的了解(見《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燕京學報》第十九期)。1945年;董作賓氏發表《殷歷譜》;他所制訂的祖甲和帝乙、帝辛三王的祀譜;编排極爲周密;但對譜中五種祀典所作的釋義;如“彡”爲“伐鼓而祭”;“翌”爲“舞羽而祭”;“祭”爲“以肉爲祭”;“”爲“用食物(黍稷)以祭”;而“”則“卜辭中以爲協合字”;在最後舉行;或同時聯合他種祀典一倂舉行”;如此云云;不免使人有含糊籠統之感。“事死者如事生”(《禮记·祭義》)是祖先祭祀的通義;黍稷酒肉是凡祭所必備之物;豈可以此等作爲一係列巨典相互區别的唯一特徵。三家以外;在字義考釋諸書中;就個别祭名進行研討;颇有勝義可採。但總的看來;這方面的研究;“雖有所發展;而進度有限”。殷人重祭;卜辭涉及的祭名既如此之多;一代祀典必甚可觀;與其以意補苴;不如蓋阙待證;也只有期望後人的深入探索。
西周的彝銘裏也有很多祭名;聯紧起來考察;其因襲之跡比較明顯。殷和西周的全部祀典目前還無法一一考查明白;而其中幾個主要的祭禮如烄 (郊)、土(社)、帝(禘)、衣(殷)、(烝);可以相信自殷至春秋一直被王朝所奉行。
(一)烄 (郊);是野外祭天的禮典。卜辭有:“癸已卜;今曰烄 ”(《殷虚文字甲编》895)。“烄 ;此();又雨”(《鐵雲戴龜拾遗》8·2)。“貞烄;中从雨。勿烄;亡其从雨”(《殷虚書契前编》5·33·2)。祭天于郊;燔柴升煙;在山上或平原築壇舉行;故問及晴雨。又“丁酉卜;(要)帝吉”(《殷契粹编》1268)。郭沫若氏謂“要殆假爲郊;書讀爲;謂郊祀上帝以也。”彝銘有《大盂鼎》:“酉(酒)無敢;有()(烝)祀;無敢(擾)。”(《大係》錄编18)郊祭亦稱祭;燔卜辭謂之;“今丁酉夕豕方帝”《殷契佚存》508)。本是祭法;燔柴取其煙火;也有置牲體于積木之上而焚之;故卜辭又有“口口口貞:四羊四豕;卯四牛四口”(《戩壽堂所戴殷虚文字》25·8)。(烄)像人交足坐于火上之形;也有用人犧的。《尚書·召誥)云:“越三曰丁已;用牲于郊;牛二。”《國語·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郊禮自殷至西周相沿不替。東周時;《春秋》记述魯僖公三十一年起舉行過多次郊祭;也有“卜郊不從乃不郊”的记載。《公羊傳》云“魯郊非禮也”;說魯君僭越;正見郊禮爲王朝巨典。
《禮记》有很多有關郊禮的闡述;《禮運》云:“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器》云:“饕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贵誠也。”有了《郊禮》書本;才能有這補經未備、闡經未明的傳记的撰作。
(二)土(社);是封土祭地的禮典。卜辭有:“癸亥卜;又土;羊一小;”(《戩》1·1)。“貞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沈十牛。”(《前》1·24·3)彝銘有《》:“王立(位)于宗土;南鄉”(《商周金文錄遺》167)。舉行祭地之禮;或說在城中;或說在北郊。“貞勿年于土”(《前》4·17·3)。王國維氏定土爲邦社是對的。邦與封音義並通(《論語·季氏》“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李賢注:“封謂聚土爲壇。”《小爾雅·廣詁》:“封;界也。”《周禮》封人職:“掌設王之社壝 ;爲畿封而樹之。”鄭注:“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墨子·明鬼下》:“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叢)社(原作位;據王念孫校改)。”這樣說來;社就是封土高起爲壇;壇之四周又壘土爲庳垣(矮牆);有門有牖;成宫形;上無屋頂;外植叢樹;它是邦國都鄙分疆劃界的象徵。《詩·綿》云:“乃立冢土。”毛傅:“冢土;大社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這是王社。《左傳》定公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這是國社。《禮记·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說文》示部:“社;地主也。”社祭是各級奴隸主祭其所書土地之神。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禮记·祭法》云:“瘗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這兩種祭法(血、埋);雖亦見于卜辭而不用于社祭;可見祀典的發展中祭法的變化最大;前後對照;十九不合。《禮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禮運》云:“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都是解說已佚《社禮》經文的傅记。
(三)帝(禘);是祭祖先以配上帝的禮典。卜辭有:“貞;年于上甲;帝;三;卯三牛。-月”《殷虚書契續编》1·3·1)。“貞帝于王亥。”(《殷虚書契後编》上卷19·1)“貞勿帝;十二月”(《粹》895)。彝銘有《刺鼎》:“唯五月;王才(在)口;辰才丁卯;王啻;用牡于大室;啻邵(昭)王”(《大係》錄编31)。《大》:“用啻于乃考”(《三代吉金文存》8·44·3)。《尚書·君奭》云“殷禮陟配天”;殷人認爲王死升天;喪禮結東、吉禮開始;即舉行禘祭;以先王配祭上帝;故《禮记·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禮本是王朝巨典;西周以後;配天之義逐漸遺落;而諸侯也僭用此禮;故《論語·八佾》有孔子“禘自既爟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之語。《春秋》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西;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衹作喪禮結東後、嗣君致先君或先妣之神主于大廟的祭禮。
鄭玄《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大廟之禮;曰用丁亥”;佚禮中有《禘禮》首句殘文;足證關于諦禮曾撰成書本;但在秦火中亡佚了。
(四)衣(殷);是合祭歷代祖先的禮典。卜辭有:“癸未王卜;貞彡曰自上甲至于多后;衣。”(《前》3·27·7)“癸亥[卜;口貞]甲子氣翌曰自上甲衣至于多后;亡三月。”(《粹》85)“王賓且乙、且丁、康且丁、武丁衣。”(《後》上20·5)“丁酉卜;貞王賓口自上甲至武乙;衣;亡尤。”(《後》上20·7)彝銘有《大豐》(當作《天亡》):“天亡又(右)王;衣祀王不顯考文王;事喜(熹)上帝。”(《大係》錄编1)殷和西周都有殷祭。但《大豐》记武王舉行殷祭而不及先公;已與殷禮不同。東周以後;據《禮记·曾子問》“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雖仍在舉行而義微有異。《曾子問》又云:“袷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則已改稱袷祭。《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明明是禘祭;而《公羊傳》却說:“大事者何?大袷也。大袷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由此曾導致以後漢儒三年一袷、五年一禘、禘袷並爲殷祭的爭議。
(五)(烝);是薦新于宗廟的禮典。其字甲骨文作、、、;金文作、等形;後世段烝爲之。卜辭有:“甲午卜;[其]黍[于]高且乙”(《粹》166)。“甲辰卜;來;……用”(《佚》877)。‘癸卯卜;禾乙且(且乙之倒文)”(《粹》908)。“己巳貞;王其南囧(明)米”(《甲》903)。“辛酉……翌曰癸;新鬯;王[受又]”(《粹》912)。彝銘除上引《大盂鼎》外;還有《段》:“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鼒(在)畢”(《大係》24)。稻麥登埸;新酒成熟;先要薦進于宗廟;讓祖先“嘗新”。《逸周書·嘗麥解》云:“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於太祖。”《管子·輕重已》云:“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夏盡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可以相信這是一個自殷至春秋一直舉行的禮典。卜辭有“今(秋)”、“于(春)”(《粹》1151)的對貞;有春秋而無夏冬;殷人尚無四時的觀念;故獨有嘗新的烝祭。《詩·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注家以爲就是四時之祭;不知可信與否;事實上以後仍以烝、嘗爲主。《春秋》經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又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左傅》襄公一十八年:“十一月乙亥;(齊)嘗於大公之廟。”又襄公十六年:“春;(晉)烝于曲沃。”又昭公元年:“十二月;晉既烝;甲辰朔;(趙孟)烝于温。”根據史書记載;未必嚴格按季節舉行。但從《國語·楚語下》載觀射父所云“曰月會於龍;國於是乎烝嘗”;《左傳》作者所云“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桓公五年)來看;當時學者議禮確實曾把嘗、烝二祭安排在秋冬兩季的。後來;《周禮》的六享中列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禮记》的《祭統》《王制》排列時祭作春礿(同禴)、夏禘、秋嘗、冬烝;與上引《詩·天保》之文聯紧起來考察;差異在于原來不屬于時祭的禴、禘、祠上。由此可證;就制度發展而論;顯然只由薦新一祭演變成嘗、烝兩祭;而各種不同编排的四時祭名不過是一種“禮說”而已。
晚周禮家論述宗廟時祭往往嘗、禘並舉;《禮记》的《祭統》、《仲尼燕居》、《曾子問》等篇有關章節都把祖先正祭和宗廟薦奠之祀等同起來;不足信據。惟有《祭義》篇的闡發最爲恰當;“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這才是時祭的規模;也由此證明薦新之禮確實是十七篇以外的佚禮。
上述郊、社等祭禮所涉及祭法;有、翌、祭、、、()、洒、、血、卯、沈、埋、、喜等。就祀典來說;祭法往往構成一個節目的内容;用《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上下篇作類比;它先行食禮;即尸食九飯或十一飯;後行酳禮;即尸與主人、主婦、賓長獻酢;包涵兩種祭法。卜辭中也有一個祀典用二或三種祭法的。一種祭法可以用于兩個以上的祀典;如食禮既用于《特牲》、《少牢》;也用于《士虞禮》(《士虞》有饗尸尸九飯節)。卜辭中這種祭法也是屬于此種情況的顯著例子。
上列五個祀典雖是最重要的;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不是專門論述祀典的發展;不過舉五祀典作例子來證明自殷至春秋實行過各種祭禮。舉行祀典;必有一定的儀式;類似《儀禮》所描繪的;在當時確實存在過;可惜没有禮记錄下來。
西周鼎彝銘文涉及禮典較多;可舉錫命禮作例證。眂朝錫命;當屬朝禮。《儀禮》有《覲禮》;是王畿以外諸侯定期來朝見的禮典;那末;王任命諸侯和任命手下公卿的錫命禮肯定是一種極爲重要而經當舉行的禮典;應在佚禮之中。封爵封官是王朝重大事件;而大部分鼎彝都是王臣的祭器。《周禮》大宗伯職云“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禮记·曲禮下》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又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這些雖保晚周傳說;但奴隸主贵族上升到一定爵位;才能受王錫命、鑄作祭器;這事實應該是可信的。在所鑄祭器的銘文裏有一部分配战了錫命禮典;如《吳彝》(《大係》錄编58)所述:
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成周大室。旦;王各(格)廟。宰朏右乍册吳入門;立中廷;北鄉(向)。王乎(呼)史戊册令吳嗣庙(素)金(錦);易(錫)鬯一卣;玄衮衣、赤爲、金車、(鞃)、朱虢(鞹)(靳)、虎(幭)熏里、、畫、金甬(銿);馬三匹;攸勒。吳拜首;敢對揚王休。用乍書尹寶彝。吳其世子孫永寶用。佳王二祀。
《吳彝》外;《師虎》、《牧》、《豆閉》、《鼎》、《望》、《康鼎》、《卯》、《免》、《同》、《觶》等;内容大致相同;可視作一體。雖然還不是詳盡记錄錫命禮的全過程;但幾個主要儀注;如王格廟;宰右受命者人門即位;王呼史官册命;錫車服;受命者對揚等;應該说是完備的。王命通過命書(有的銘文兼載命詞)有錫物來表達;而臣下接受王命通過手舉錫物(即所謂“揚”)、口呼“王休命”(即所謂“對”)來致敬意。這二者十分重要;所以即使銘文較簡短的也都提及。這些銘詞正反映了禮物和禮儀兩個方面;與记錄儀式全過程的禮書不過僅有记述上繁簡不同而已。此外;《小盂鼎》(《大係》錄编19)记王命盂伐方班師告廟“飲至之禮”(郭沫若說);《駒尊》(當作《尊》;《陕西省書銅器釋》55)记王行執駒禮;二器所述俱屬軍禮。《靜》(《大係》錄编27)记王命靜教射于學宫;《書鼎(二)》(《大係》錄编39)记恭王在射盧學射;《匡卣》(《大係》錄编67)记懿王在射盧學樂舞;三器所述俱屬學禮。《噩侯鼎》(《大係》錄编90)记王與噩侯方行射禮;射前飲酒獻酢;與《大射禮》略同。這些銘詞雖甚簡略;但它所反映各種禮典的主要方面還是很清楚的。
再就鼎彝本身來講;自兩漢“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許慎《說文解字叙》)以後;歷代不斷有古器物出土;至近數十年;特别是全國解放後;國家進行有計劃的科學發掘;從遗址、墓葬、窖戴中出土了大量考古學家稱之爲“禮器”的書銅器;如鐘、鉦、鼎、鬲、甗、、簠、盨、敦、豆、尊、彝、卣、壶、盉、罍、盤、匜、鑒、爵、角、觚、觶、斝、觥等;就是上述“禮物”的一部分。“禮器”與實用器在造型上應無多大區别;把它送入墓葬或者有意識放進窖戴;顯得特别贵重;確實是實行禮典時所專用的器物。上文說明禮典是禮物和禮儀的結合;既存在這些“禮器”;而“禮儀”是禮器的使用;那末;“禮器”的存在就是各種禮典存在的鐵證。
下面我們再從先秦典籍裏求取這方面的證據。先秦典籍涉及各種門類的禮典和《儀禮》的记述絕大部分是一致的;凡在《儀禮》成書以前的记載;都屬略述一個具體禮典的舉行;在《儀禮》》成書以後的记載;始有援引其原文;這一點可以說是涇渭分明的。《尚書》的《顧命》和《康王之誥》记述了王朝巨典的隆重舉行;《顧命》记載周康王初即位的一段文字;實是朝禮的規模;《康王之誥》是康王在喪期内接受諸侯的覲見。《逸周書》的《大匡解》是和《顧命》-樣的周王朝禮之篇;而《世俘解》則记述了武王克商後舉行規模宏大的獻俘禮典。在這些篇章中;如果把记載當時具體的人和事去掉;就和禮書幾乎是一模一樣。當然;《顧命》和《康王之誥》不見得即是康王時所记;《大匡解》和《世俘解》更不見得是文、武時代的作品;但撰作于春秋以前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可以說它是先于十七篇的“禮書”。
在《毛詩》裹也有一些章君涉及各種禮典。《賓之初筵》和《行葦》詩;是對王與羣臣習射和射前燕飲的描繪;彷佛舉行燕禮和大射禮。還有《楚茨》一詩;是描寫祭祀祖先的情景;與《少牢饋食禮》、《有司》有相應之處;詩篇所反映的情形;是用于禮物和禮儀相結合的生動描繪;燼管爲了適應于文學作品的特點而不是按儀式程序來呆板敘述;因而在文字上與禮書距離較大;但就内容來看仍然相符。
《左傳》《國語》裏有很多述禮之文。雖然《左傳》的撰作時代還有爭議;但所述各國贵族實行禮典;都是春秋時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言論;不是後代人所能捏造的;何況有些事實還可以用《國語》來印證。因此;即使《左傳》出于後人之手;其事則決非虚構。我師書元弼先生云:“考之《左氏》;卿大夫論述禮政;多在定公初年以前;自時厥後;六卿亂晉;吳越迭興;而論禮精言;惟出孔氏弟子;此外罕聞。”(《禮經學》卷四《會通》)這一揭示很深刻;說明定公時社會性質開始變革;對禮典的實行;前後截然不同;可見《左傳》、《國語》所记;都是可信的。書先生又云:“按聘、食、覲禮;皆見《左傅》而聘禮尤備。”(同上)《左傳》、《國語》所记;主要是朝、聘、響禮;其次是喪禮、冠禮。
首述冠禮:《國語·晉語》“趙文子冠”;以下歷敘文子往見欒書、荀庚、范燮、卻錡、韓厥、荀瑩、郤犫、卻至、張孟;與《土冠禮》所云“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正相吻合。
次述喪禮:《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書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諸侯喪禮的歸赠;與《土喪禮》國君贈禮節“公赗玄纁東、馬兩”;雖爵位等差不相當;其助葬之義是一致的。又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粗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饗、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晏嬰以大夫而用士禮;故與《喪服》、《既夕记》合。
再次述聘禮:《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加之以敏。”又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赠賄;無失禮。”又載楚蓬啓疆云:“宴有好货;飧有陪鼎;人有郊勞;出有贈賄。”《聘禮》记述使臣到所聘國;人境接受郊勞;離境接受贈賄;二者總括出使的過程。其間歸饔餼時;賓與上介各得“陪鼎三”;而“庭實設;馬乘”; 即是宴會時的“好貨”。《國語·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聘禮》過他邦假道節:“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左傅》昭公二年:“叔弓聘于晉;致館;辭曰:敢辱大館。”《聘禮》致館節:“卿致館;賓迎再拜。”又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即《聘禮》末所附遭所聘國君或夫人世子喪節。又哀公十五年云:“(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吳人辭;)芋尹蓋對曰:‘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面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聘禮》末附出聘寶介死節云:“寶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芋尹蓋是貞子的介;堅持着當時中原諸國所守的“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和“朝聘而遭喪之禮”。《周語》云:“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蒞之;晉侯端委而入。既畢;賓、容、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此是諸侯國接待周王的來使;在儀式上雖因爵位尊卑而有所斟酌損益;但仍是合于聘禮等差推比的;所以内史興稱赞:“晉侯其能禮矣”
朝禮和饗禮都已亡佚。十七篇有覲禮而無朝禮。諸侯臣屬于天子有朝覲之禮;春秋時周天子微弱;諸侯不去朝王;朝覲禮近乎廢棄。可是諸侯之間;小國屈服于大國;也有不用會禮而用朝禮的。《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這些儀容動作的敘述;正是當時實行朝禮的佳證。還有;卿大夫臣屬于天子、諸侯;私臣臣屬于卿大夫;也要用朝禮。《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據此可知朝禮規模很大;範圈很廣;雖内容不甚清楚;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是可以想見的。
十七篇有食禮而無饗禮。饗禮是高一級贵族款待低一級贵族來見時的宴會。實行于各級贵族之間。它是一個獨立的禮典;也是某一巨典的一個組成部分 ;《聘禮》、《朝禮》即包含饗禮。劉文淇《左傅書注疏證》云:“案《左傳》多作享;作饗爲僅見。”沈欽韓以爲《釋文》、《石經》饗並作享;即《聘禮》聘享節“如享禮”之享;此說不確。《左傳》成公十四年:“衛侯饗書成叔;寧惠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享與食並舉;可證享當作饗。《國語》亦享、饗同作。據《長盉》“穆王才;穆王鄉豐”(《遗》293)。《師遽彝》(懿王時器)“王才周康;饗醴”(《大係》錄编70)。西周時既實行此禮;春秋時實行此禮是無可懷疑的。《左傳》莊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公二十五年:“四月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又二十八年:“五月已西;王享醴;命晉侯宥。”《晉語》:“(襄)王饗醴;命公胙侑。”《左傳》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又僖公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周惠王、襄王、定王都爲諸侯或陪臣舉行過饗禮。饗禮用樂;《左傅》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穆叔所以不拜;《魯語》比《左傳》講得明白:“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是爲爵位等級上不可差忒的緣故。對整個饗食;《周語》记有定王的一段赞詞:“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幂;敬其祓除;體解節折 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货;以示容合好。”此處所闡發的這個禮典的意義是很明確的。至于《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所載“丁丑;楚之人餐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晉語》所載“(曾文公)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都在賓主等級關係上不合規程;但可借以知道王饗元候是用九獻、 庭實旅百和加籩豆六品的。比起《朝禮》來;《饗禮》的遺留要多一點;當然還是殘缺的。
以上對比《左傳》、《國語》所述冠禮、喪禮、聘禮與《儀禮》書本相應;而朝禮、饗禮也獲得充分的根據;都證明春秋時這些禮典在現實生活中經當舉行。清代顧棟高撰《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七);以爲“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傅所未經見”;說没有援引《儀禮》原文是對的;但對上述各点的述禮之文熟視無睹;一筆抹煞;輕率地作出“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輯無疑”的結論;顯然不是尊重客觀事實的正確態度。更有姚際恒者;雖然看到了這些记載;但他却據以作出相反的結論;以爲《儀禮》是後人述春秋時事而抄《左傳》之文來编造的。把整理和记錄正在實行的禮典說成有意的捏造;那末爲君么他們不把朝禮、饗禮也一起编造出來呢?可見這些都是不作寶事求是科學分析的偏頗之見。
無論《尚書》、《逸周書》、《毛詩》或《左傅》、《國語》;都能證明春秋以前各種禮典仍在實行;而最能具體而確鑿地證明禮典先于禮書而存在的;莫過于《論語》一書。《論語》述禮之文不下四十餘章;可以明顯地看出:孔子時禮的書本還没有撰作;而禮物和禮儀所構成的禮典正在普遍實行。下面把這些述禮之文分四大類來作具體分析。
第一類是指斥當時的違禮行爲:(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了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3)“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子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4)“子曰:禘;自既爟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5)“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赐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6)“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焉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以上《八佾》)(7)“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子罕》以上七條;只有(7)見于《燕禮》和《大射禮》。其餘雖都不在十七篇中;但有些也能約略地考查出來;如以《燕禮》徹俎時“奏胲”來推比;“三家者以雍徹”是天子祭祖宗的禮典。本來;只有被認爲合于等級制度的禮典在實行;才能被據以判斷某些儀式是不合規程的;否則就談不上君么違禮不違禮。七條所述都屬禮物和禮儀;可以充分證明孔子時各種禮典都在實行;同時根據(7)條來看;它不是《儀禮》原文的引述;又可證當時禮書還不存在。
第二類是某些禮儀的概念:(1)“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2)“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先進》)(3)“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闻之矣。(《衛靈公》)(4)“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壤;三年不爲樂;樂必崩;魯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禭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闻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陽貨》)這些是射禮、祭禮、喪禮的概括;如果當時没有實行過這些禮典;決不可能憑空造作得出來的。但又絰毫没有援引《儀禮》原文的痕迹;同樣說明禮書還不存在。
第三類是有關禮的理論和禮的作用的闡述:(1)“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政》)(2)“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贵。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3)“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4)“子人太廟;每事問。或曰:執謂鄹人之子知禮乎?人太廟;每事問。子闻之曰:是禮也。(以上《八佾》)(5)“不學禮;無以立。”(《季氏》)“興于詩;立于禮;成于學。”(《泰伯》)“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6)“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陽貨》)(7)“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8)“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9)“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這些有關禮的闡述;都是從具鹘禮典中抽象出來的。如果没有禮典的存在;這就無從談起。
第四類是“容禮”;集中记載在《鄉黨》篇内。所謂容禮;就是:在參加禮典中;依據自己的等級身份在每個儀節上表演最適當的儀容動作;例如在朝禮中:“朝;與卜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又如在聘問禮中;擔任君與别國使臣間傳話的擯者:“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奉使到别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在曰當生活中;同樣注重合乎規程的容色;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阵階。”見齊縗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這些都是禮儀最具典型的部分;用文字表達終欠顯豁。容禮在禮書撰成以前;可與禮典結合;也叮以單獨表現;在禮書撰成以後;仍然單獨流傅;西漢初年;“徐生善爲容”與“高堂生傅士禮”並行;所以朝廷有禮官大夫、郡國有容史的設置。據此更易看出:禮物、禮儀(包括容禮)與禮書是兩回事;不可混爲一談;而禮物、禮儀所構成的禮典並不依靠禮書而存在的。
把《論語》一書有關禮的记載加以分析和綜合;可以證明一個事實:在春秋以前;禮物與禮儀相結合的各種禮典自在各級贵族中普遍實行。孔子是知禮者;擔任過贊禮(擯、相)一類的職務;所以在他和弟了們的問答中反映了那么多禮的理論和禮的實踐;但在他所有有關禮的言論中没有直接援引《儀禮》的原文;有力地證明其時禮書還不存在;各種門類的禮典還没有禮记錄成文。過去有人主張禮制作以後才會有禮典的實行;這種說法與事實恰恰相反;因而是錯誤的。
經過出土實物和先秦典籍各方面的檢驗;完全證實殷、西周到春秋;由禮物、禮儀所構成的各種禮典;自在奴隸主贵族中普遍地經當舉行。
三
上文揭示了一個爲歷代禮家所忽視的重要事實;殷、周奴隸主贵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經當舉行着各色各樣的禮典;禮典重在實行;没有记錄成文。于是;聚訟千載的《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在何時撰作的問題;有可能由此而得到解決。
從分析《論語》述禮之文以證實孔子熟習各種禮典而其時《儀禮》還没有撰成書本;而《禮记·雜记下》裏有一則记載;時間正相銜接;事實恰好合榫。其文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土喪禮;《士喪禮》於是乎出。”注家狃于周公制禮之說;所釋多迂曲難通。各級喪禮從來自在各國實行;春秋後出現土用卿大夫制的僭上行爲;哀公命孺悲釐訂士喪禮;“於是乎書”;明白無誤地表明在此時才寫成書本。某些學者斥爲“何足爲據”;是不顧前後史實的粗暴否定。《雜记》是喪禮的傳记;相繼述作;既然他能闡發喪儀蕴義;當然也應知道《士喪禮》等篇爲何人所作;不過類似篇章中惟有《雜记》作者有此记述而已。
喪禮内涵喪、葬、祭三個部分。《土喪禮》上篇不僅與记述葬禮部分的下篇《既夕》相連成文;不可分割;而且還必須包括记述葬後虞、卒哭、小祥、大祥、禫等喪、吉諸祭的《土虞禮》;方能成爲完整的三年之喪。而《喪服》一篇本是密切配合這三篇的:《士喪禮》记親喪第三日大殮“成服”;即是依據《喪服》條文來確定所有内外親的服制;《既夕》记葬後舉行三虞喪祭、卒哭吉祭後的除去重服;改受輕服;《士虞禮·记》记滿一年小祥祭後去首服用練冠;滿兩年大祥祭後除衰服用朝服;二十六個月禫祭後恢復當服;都是按照《喪服》行事。如果祇有《士喪禮》上下篇是不成其爲喪禮的。既如此密切相關;必在同時撰作;“《士喪禮》於是乎書”;應該總括四篇;都是孺悲所记録。《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歳而反乎魯。”其去魯之年;《史记》所记有定公十二年《魯周公世家》、十三年(《衛康叔世家》、十四年(《孔孑世家》三说;江永《鄉黨圖考》考定爲十三年;則返魯在哀公十一年。《春秋》哀公十六年云“孔丘卒”;然則孺悲從孔子問禮在十一年至十六年間;從學習到撰作應有一段時間;四篇寫成書本當在哀公末年至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公元前五世紀中期。
殘存十七篇除去上述四篇以外的十三篇在何時记錄成文;已無法一一考定;已經亡佚的若干篇于何時撰作;更無從談起。根據《曲禮下》所脱“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華讀祭禮;喪復當;讀樂章”;在《曲禮》作者手裏;《士喪禮》、《既夕》、《喪服》等喪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等祭禮;都和《詩》(樂章)一樣有書本可讀;除了給上述孺悲撰作《士喪禮》四篇添一有力旁證外;更可據以推斷孔氏後學繼孺悲之後紛紛撰作;各種禮典的基本是在一段較長時間之内由很多人陸續寫成的。
考查先秦典籍的撰作;有許多不可能推定確切的年歲;但應力求約略確定在某一段時間之内;也就是確定撰作時代的上下限。《土喪禮》四篇是《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中最早寫成甚本;上文考定它撰成于周元王、定王之際;就是《儀禮》撰作時代的上限。
下限比較難于確定。近人對十七篇的撰作時代作過推测。錢玄同說:“其書蓋晚周爲荀子之學者所作”;“五經之中;當以《儀禮》爲最晚出之書”(《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题》)。洪業說“高堂生傳本;编纂于荀子之後也“(《儀禮引得序》)。但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證據;因此未必就能一言論定。
考證不知撰人的古代典籍;根據它曾被其他典籍援引來推究比勘撰作時代;雖不敢說是唯一可靠的;但至少不失爲比較客觀而切實的方法。當然;《儀禮》具有不同于他經的特點;如胡培翚所云“夫《儀禮》之書;叙次繁重;有必詳其原委而義始見者;非若他經之可以斷章取義也”(《研六室文鈔》卷三《儀禮非後人偶撰辨》)。其書都是整章整節记錄一個完整的儀注;截取一句二句;不能明瞭其意義;因此援引其文;既不便全章全節的迻錄;就只能剪裁删節其文而概述其義。某些人不瞭解禮文的這個特點;無視這種經過剪裁删節的引文;武斷地認爲羣書少有稱引。而顧棟高論《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以爲“《詩》《書》三傳所未經見”;是個最具典型的例子。其實;和其他典籍一樣;當《儀禮》本出現于學者之間而產生了影響;豈有不被人引述之理;不過引述者對“禮”文和《詩》、《書》之文在處理上根據各自的特點而有所不同。
最早徵引《儀禮》之文是《墨子》。
《墨子》的《節葬》、《非儒》、《公孟》三篇節引《喪服經》文而以《節葬卜》所引最爲完整: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這就是《喪服經》斬衰章的君、父、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和齊衰章的父卒爲母、母爲長子等條。《喪服》夫爲妻正服列于杖期章與此文“妻”字不合;《非儒下》雖無妻字但下有“妻、後子與父同也”句;則此妻字並非傅抄寫誤。《左停》昭公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是指周景王有穆后和太子壽之喪;當時丧期上實有爲妻三年的異說;墨子書有此记載是不足怪的。(《墨子·間詁》引諸家說均誤。)但是;服制上妻爲夫三年爲斬衰正服;此文中不愿獨缺;故仍應定妻當作夫字。“死者五”;王引之改“者五”爲“五者”;俞樾改“五”爲“二”;孫詒讓以五字下屬;均誤。五指父爲長子、妻焉夫、妾焉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爲長子五種三年服。《節葬下》又云:
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
這就是《喪服經》不杖期章的世父母、叔父母、昆弟、眾子、昆弟之子等條。又云:
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
這就是《喪服經》小功章的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大功章的姑姊妹適人者和緦麻章的舅、甥等條。
《喪服經》的體裁;如贾公彦疏所云“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徵引其文;很難就原文摘句。《墨子》概述其義;不得不加以剪裁删節;儘管字句與原文不盡相符;但總括全經;對五正服中的主要守服者並無遗漏和歧出。只要和《論語· 陽货》宰我問喪章相對照;不難看出;彼文泛論三年之喪;不是援文立说;而此文則句句落實;如果没有書本作依據是做不到如此具體而詳盡的。
《墨子·貴義》云:“子墨子南遊于楚;见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孫詒讓《間詁》云:“畢云;檢《史配》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頰聚》引作惠王;是。义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此文捝佚甚多;余知古《諸宫舊事》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此與《文選》注所引合。疑故書本作‘獻書惠王’;傅寫捝書存獻;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蘇云;楚惠王以周敬王三十二年立;卒于考王九年;凡五十七年。墨子之遊楚;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諸宫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十九年也。”據此可見魯悼公末年; 《墨子》已有部分成書。“節葬”、“非儒”是墨學的中心課题;這時《節葬》等三篇必有一或二篇已經寫成;而文中有引《喪服》原文;可見孺悲在悼公初年撰作的《士喪禮》等四篇;十多年後已經流傅;墨子手中有其傅本。
《孟子》和《荀子》都徵引過《儀禮》之文。
孟軻是孔子的私淑弟子。趙岐《孟了题辭》說他“通五經;尤善于《诗》、《書》”。書中引《書》凡二十九;引《詩》凡三十五;而很少議論禮、樂;述禮之文只有二則;《離婁下》篇云:
(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
顯然引自《喪服經》齊縗三月章“焉魯君、君之母妻”。又《萬章下》篇云:
孟子曰:在國曰市書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禮也。
此文與《士相見禮》“宅者;在邦曰市書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相同。二文俱明言“禮”;可見他手中有《儀禮》書本。
荀況是戰國後期的禮學大師。《禮論》《大略》是他的述禮專著;《禮論》當屬自撰;《大略》則出于弟子雜錄;都是論述昏、喪、祭、饗諸禮的。其體裁與《禮记》很相似;往往前引《儀禮》之文而後申以己说;對原文頗多剪裁删節;但並列對照;並疏解其異文;就能看出荀況禮學是依《儀禮》立說的。
《儀 禮》 | 《荀子》 | 疏 證 |
屬纊;以俟絕氣。(《 既夕·记》) | 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己。(《禮論》) | 案:楊倞注:“紸;讀爲注;即屬纊也。” |
外御受沐人。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蚤揃如他日。器用鬠。(《士 喪》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士喪》) | 始卒;沐浴;鬠;體;饭含;象生執也。(《禮論》) 饭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禮論》) | 案:尸不冠;以組東髮;不加簪;削之鬠。又:體;杨倞注“謂爪揃之屬”;即鄭玄注“断髪揃鬚也”。又案:楊倞:“生稻;米也。槁骨;貝也”。
|
瑱;用白纊。(《士喪》)瑱塞耳。(《既夕·记》)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里;著;組係。(《士喪》) | 充耳而设瑱。(《禮論》设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禮論》) | 案:鄭玄注:“瑱;充耳。” 案:楊倞注:“儇與還同;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用方尺二寸帛;兩層縫爲組;緇面䞓襄;并充以新綿;覆于尸面;謂之幎目。後用長五尺的練帛裹尸首;削之掩面。笄有二;安髪之 |
笄名鬠;固冠之笄名簪。斂不用冠;則不用固冠之笄 | ||
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士喪》) 徹褻衣;加新衣;設明衣。(《既夕·记》) | 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禮論》) | 案:褻衣是親膚之衣。明衣是新製的褻衣。 《荀子》的“說(脫)褻衣”;即《既夕》的“徹褻衣” |
爲銘;書銘于末曰某之某之柩。重木;刊穿鑿;甸人置重于中庭。祝取銘置于重。(《士喪》) | 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禮論》) | |
主人奉尸斂于棺;乃蓋。(《士喪》) 三日成服。(《士丧》)
| 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禮論》)
| 案:掘肂于西階上;大斂後置棺斂中。西階賓位;故曰殯。大斂在喪之第三日;成服在第四日。不數死日;则殯在第二日;成服在第三日。 |
商祝饰柩;一池;紐䞓輕後緇;齊三採;無貝。|(《既夕》 巾奠;乃牆。(《既夕·记》) 燕器:杖、笠、翣。(《既夕》)
| 無帾丝歶缕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禮論》
| 案:杨惊注“無融爲幠”;與荒通;亦稱柳;是覆蓋在柩上的布幕。注“帾與褚同”;亦稱牆;是圍在柩四周的布帷。即鄭玄注所云“饰柩;爲設牆、柳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紐所以聯帷荒。”又案:杨注:“或日絰讀爲綏;歶讀爲魚;謂以銅魚懸于池下。”鄭注:“池者;象宫室之承霤;懸于柳前。”經過疏解;上列二文大致相合。 |
《儀 禮》 | 《荀子》 | 疏 證 |
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縮三。(《既夕》 | 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禮論》) | |
君使人禭;禭者左執领;右執耍;入;升致命。禭者入衣尸。親者禭;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朋友禭;親以進。有禭者;則將命;賓入;中庭北面致命。朋友親禭。如初儀。(《士喪》) 公赗玄纁東;馬兩。賓赗者;將命;馬人設。若赙、賓東面將命。赠者;將命。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則赗而不奠。知死者赠;知生者賻。(《既夕》) | 赙赗所以佐生也;赠禭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大略》) | |
父醮子;命之;辭日: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做先妣之嗣;若则有當。(《士昏·记》)
|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當。(《大略》) | |
多財则傷于德;幣美则没禮。(《聘禮·记》) | 聘禮志日:幣厚则傷德;財侈则殄禮。(《 大略》) | |
若不言;立则視足;坐则視膝。(《士相見》) | 坐視膝;立視足。(《大略》) | |
(佚郊褛) | 郊者;並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禮論》) | 案:此與《禮運》“定天位”、“百神受職”同意;乃《郊禮》本義。 |
(佚饗禮) |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王制》) | 案:以《公食》證《饗禮》;其義大致相似。 |
《荀子·勸學篇》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楊倞注:“數;術也。經謂《詩》、《書》;禮爲典禮之屬也。”從其所言“讀禮”來看;手裏有着今存《士喪》、《既夕》、《士相見》以及已佚的《郊禮》、《饗禮》等本。可見《儀禮》各篇已在習禮經師中廣泛流傅。從《論語)的“執禮”到《荀子》的“讀禮”;就是各種禮典從贵族實行到經師撰作本的發展過程。《禮論》篇以禮名篇;稱“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又云“喪禮之凡“;《大略》篇又引《聘禮志》;其同于《儀禮》之文;不言可喻;是出于他的援引。因此;《儀禮》不是“爲荀子之學者所作”。
徵引《儀禮》原文最完整、最詳備的當推二戴(戴德、戴聖)所輯的《禮记》。
爲了論證上的方便;在核校二戴所輯《禮记》援引《儀禮》原文之前;有必要解決《儀禮》各篇篇末所附之“记”與本經具有何種關係的問題。今存十七篇中十二篇篇未有附“记”(《士喪禮》上下篇的“记”集中在《既夕》篇末;表面上看是一篇;其實是通乎上下的;應該說十三篇有附“记”);就其内容而論;一是闡發禮的意義;二是追述遠古異制;三是詳述因故變易其制的不同儀式;四是備載因爵位不同而引起器物、儀式的差異;五是敘說所用器物的製作、形狀和數量;六是记錄禮典所用的“辭”。因此歷代禮家都以爲:經文是叙述-個禮典的始末;记文是補經之作;從而把它與二戴所輯《禮记》相等同。誠然;在闡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這一點上它與二戴《禮记》是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從與本經的關係上看;由于附經之“记” 與經的界線很不清楚;有些問題一直感到無法理解;也無法解決。例如:一、十七篇中四篇無“记”;但與有“记”之篇相對照;有些章節不像是經文;如《士相見禮》篇末的進言之法節、传坐於君子之法節、稱謂及執鷙之容節;顓屬记文;因其篇無记字而被當作經文了。二、同類的章節;有的在經文而有的在记文;如《士冠禮》經文有“冠辭”、“醴辭”;而《士昏禮》六禮之辭俱入记文。又如《特牲饋食禮·记》有“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云云;而《鄉射禮》經陳設節有相同的設洗設篚之文。又如《士昏禮》、《公食大夫禮》俱有附记;《土昏禮》“若不親迎”在记末;《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在經未记前。三、如果附經之“记”屬于補經之作;那末有的經文單獨來看就顯得殘缺不全了。以《喪服》爲例;如缺少记文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等條;就不是完整的服制;以《士昏禮》等爲例;賓主之辭在记内;记文後作;當時就無辭可用了。四、可能出于同樣的原因;後世的學者對經和记也不曾加以嚴格的區分;有人把记當作經;如《禮记·問喪》引“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通典》卷七十二引《石渠議奏》“經云宗子孤爲殤”;都見于《喪服记》;而《問喪》作者和戴聖都把它當作經。有人把經當作记;如鄭玄《詩·采蘩》箋引《少牢》經文云“禮记主婦髲鬄”;郭璞《爾雅·釋言》注引《有司》經文云“禮记曰厞用席”;二者都是經文而鄭、郭稱之爲记。還有引述记文而或稱禮或稱记;如何休《公羊傳》隱公元年“隱長而卑”解詁引《士冠·记》文;稱“土冠禮曰”而不言记;而閔公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解詁引“士虞记曰”又正言记。凡此等問題;歷代禮家雖多方辯解疏通;但始終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解釋。1958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西漢簡本《儀禮》七篇九卷;其中《喪服》、《特牲饋食禮》、《燕禮》三篇有附經之“记”;而經记之間;不但没有如今本標有“记”字;而且所標“口”“○”符號與經文分章符號相同;顯然不是用來區分經、记的特殊標志。從簡本上受到啓發;恍然領會《儀禮》本經篇末所附之“记”;不過把行文上不便插人正文的解釋性、補充性的文字;在後人可以用雙行夾注或加括弧來處理的;在它就安排在篇末作附錄。《問喪》作者和戴聖等所看到的傅抄本可能也和漢简本一樣没有“记”字來劃分前經後记。有漢簡本作證;今本“记“字顯然是漢以後人所加;不足憑信。附經之“记”本來就是經文的組成部分;“於是乎書”時便已包括在内;經與附經之“记”不是前後撰作的兩種書;而是同時撰作的一書的兩個部分;因此;援引附經之“记“與援引本經之文就不必再加以區别了。
二戴所輯《禮记》是《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傳记;即皮錫瑞所謂“弟子所釋謂之傳;亦謂之记”(《經學歷史》二)。非當明顯;它是依據《儀禮》書本來解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的。《漢書·藝文志》禮類列“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记也。”《經典釋文·敘錄》注引劉向《别錄》云:“古文记二百四篇。《隋片·經籍志》云:“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十一篇、《樂记》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明堂陰陽记》以下四種亦見于《藝文志》;可見《別録》所稱二百四篇;亦必包括這些篇章在内。篇數有參差;不過出于分合的不同;不足深究。但値得注意的是;從這裏反映出一個事實:七十子後學者所撰之‘记”;在當時單篇傳抄;未曾匯輯成書。因此;流傳到西漢初年;滲入了若干篇秦、漢間人的著作;如鄭玄《三禮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又如《史记·封襌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而《大戴禮记·保傅》與賈諠《新書》的《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禮察》“凡人之知”以下與《治安策》均文多相同;當是從賈誼書滲人的。又《禮记·中庸》爲子思所作是可信的;但被秦人竄加了“車同軌、晝同文”等句子(從金徳建说)。又《大戴禮记·公冠》“成王冠”以下亦漢代禮家述禮之文;而《盛德》前半篇爲戴德自撰之作。這樣;使“记”文的内容更加複雜;而撰作時代就不易考定。《禮记正義》大題下引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记八十五篇;戴聖傳记四十九篇。”二戴各自輯爲《禮记》。儘管沙汰了百來篇可能是内容淺陋的篇章;但一些秦、漢間人的作品依然人錄。《大戴禮记》今存三十九篇;起第三十九;終八十一;中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御覽》卷五百二十九引“《五經異義》曰大戴說《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今小戴《禮器》竈作奥。《詩·摽有梅》孔疏云:“案《異義》人君年幾而昏;今大戴說云云;《禮·文王世子》云云。”阮元《校勘记》引浦鏜云:“《異義》所據;《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也。《豳譜》及《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據。”《公羊傅》襄公十六年何休解詁引《玉藻》“天子旂十有二旒”云云;《白虎通·喪服》引《大傅》“父母之葬居倚廬”云云;又《崩葬》引《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云云;又引《雜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云云;又《情性》引《禮運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云云;皆不見于小戴所輯《禮记》。此等佚文;丁晏《佚禮扶微》搜集甚完備;說者援《異義》之例;以爲《大戴禮记》之逸篇。然則大戴所辑《禮记》;亦有《记器》、《文王世子》、《大傳》、《檀弓》、《雜记》、《禮運》等篇;與小戴所輯;不過句有出入、文有異同而已。至于現存之篇;二戴《禮记》亦有重複;《哀公問于孔子》與《哀公問》全篇相同;《禮察》開頭“夫禮”至“舞矣”一百三十多字見于《經解》;《本命》“有思”至“教也”二百七十多字見于《喪服四制》;二记都有《投壺》篇;其文大致相同而末段互見有無。從佚文和重出兩方面推比;可見今本《大戴禮记》所缺;有的即是今本《禮记》之篇。而晉、唐人所說戴聖删戴德之爲小戴记之說(見《經典釋文·敘錄》引陳邵《周禮論序》和《隋書·經籍志》;當亦自有所據;未必全出虚構。《禮记》至二戴始匯輯成書;今稱《大戴禮记》;古稱《大戴禮》)或《大戴记》;今稱《禮记》;古稱《小戴禮》或《小戴记》。其實;應該稱爲“大戴輯《禮记》”、“小戴輯《禮记》”或“一
戴輯《禮记》”;表明此是漢人輯前代之文。
二戴所輯《禮记》内容龐雜;說它是《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傳记;恐不易爲學者所接受。我師書元弼先生云:“二戴记之說禮;大類有三;曰禮、曰學、曰政。《曲禮》、《檀弓》、《遷廟》、《釁廟》、《冠義》、《昏義》、《朝事義》等篇;禮類也;《學记》、《中庸》、《儒行》、《大學》、《曾子》十篇;學類也;《王制》、《月令》、《夏小正》、《文王官人》之等;政類也。”(《禮經學》卷四《會通》)按三大類來區分大戴輯《禮记》三十九篇、小戴輯《禮记》四十九篇;就能使各篇何者當屬禮類;何者當屬政、學類;性質明確;界線清楚。政、學類諸篇及《樂记》可置勿論;秦、漢人之作應予剔除;列入禮類的;小戴所輯有:《曲禮》上下、《檀弓》上下、《曾子問》、《禮器》、《郊特牲》、《玉藻》、《喪服小记》《、《大傳》、《少儀》、《雜记》《上下、《喪大记》《、《祭法》、《祭義》、《祭統》、《仲尼燕居》、《奔喪》、《問喪》、《間傅》、《三年問》、《深衣》、《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大戴所輯有:《禮三本》、《虞帝德》《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投壺》、《公冠》《、《本命》等;凡三十九篇。經過這樣的篩選;《禮记》是《儀禮》的傳记這個事實方能顯現出來。其中加有《符號的專爲某一禮典解說之篇;如《冠義》之於《士冠》《昏義》之於《士昏》等;此種關係尤爲鮮明。爲說明傳记是解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試爲列表如後。但傳记往往引述禮文而後加解說;因此引文較多;難以全錄;只能每篇選取一節與《儀禮》原文對照參觀。
《儀禮》 | 二戴輯《禮记》 | 疏證 |
冠者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 (《士冠》) | 見于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冠義》) | |
昏禮;下達;納采;用雁。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主人如寶服;迎于門外。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寶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寶入授;如初禮。納吉;用雁;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東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雁;告期;如納徵禮。(《士昏》) |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人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昏義》) | |
《儀禮》 | 二戴輯《禮记》 | 疏證 |
凡传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士相見》) | 传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少儀》) | |
尊兩壶于房户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鄉飲》)薦酺;五挺;横祭于其上。出自左房。(《鄉飲·记》) | 鄉人士君子尊于房中;賓主共之也。東有玄酒; 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洗當東榮;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鄉飲酒義》) | 案:左房右室; 在東;故左房即東房 |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燕禮》) | 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燕義》) | |
公尊瓦大兩。(《燕禮》) | 君尊瓦甒。(《禮器》) | |
兩壶獻酒。(《大射》)
| 汁獻涚 于醆酒。(《郊特牲》)
| 案:鄭注:“獻讀爲沙;沙酒濁;特之;必摩沙之也。 |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東帛勞。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内。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公侧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间。(《聘禮》) | 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内而朝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 (《朝事》、《聘義》) | 案:《朝事》誤脱命字;《聘義》誤脱讓字;又朝作廟。又案:卿爲上大夫;卿郊勞即大夫郊勞。 |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聘禮》) |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朝事》、《聘羲》) | 案:《朝事》承作丞;脱“土爲紹擯'句。 |
上介不襲;执圭;屈繅。(《聘禮》) | 执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则襲。(《曲禮下》) | 案:繅即藉;屈缫即有藉。 |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聘禮》) | 既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内;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所以厚重禮也。(《朝事》、《聘義》) | 案:《聘義》既作餼。
|
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酱、魚膾。(《公食》) |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鮨、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酱、魚膾。(《内則》) | 案:鄭注:“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则膮、牛炙间不得有醢;醢衍字也。”據鄭校知“牛膾”鄭本亦作“牛鮨”;其誤在鄭氏以後;否則注當有校文。 |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至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日升;升成拜。(《觐禮》) | 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朝事》) | |
《儀禮》 | 二戴輯《禮记》 | 疏證 |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觐禮》) | 肉袒人鬥而右;以聽事也。(《朝事》) | |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缨、菅屨者:父;君。(《喪服》) | 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丧服四制》) | 案:喪服十一章;首章不言“三年”以次章齊衰章言三年;则首章三年可知。 |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缨、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喪服》) | 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喪服四制》) | |
緦麻三月者:妻之父母。(《喪服》) |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服問》) | 案:《服傳》云:“何以緦;從服也。” |
後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日:“皋!某复。”三;降衣于前;受以篚。後者降自後西榮。(《士丧》) | 小臣後;士以爵弁;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丧大记》) | 案:此文總述作、大夫、士三種喪禮。此取士級;用小臣、司服;顯有未合;鄭注“復者;有司也”是也。 |
楔齒用角柶;缀足用燕几。帷堂。商祝徹楔受貝。祝又受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卒斂;徹帷。(《士喪》) | 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丧大记》) | 案:士亦當用有司。 |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士丧》 | 喪服之先散帶也。(《禮三本》) | 案:亦見于《荀子· 禮論》;帶作麻。《士喪》贾疏云:“此小斂絰有散帶垂之;至三日成服絞之。”絞謂糾而合之;初喪以一根麻爲首絰;一根麻爲腰絰;腰絰象大帶未糾合;故稱散帶。 |
尸又三饭;舉肩;祭如初;舉魚臘俎;俎釋三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士虞》 | 成事之俎不嘗也。(《禮三本》 | 案:亦見于《荀子· 禮論》。《士虞记》云:“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虞祭畢謂之成事;其俎曰成事之俎鄭注:“釋猶遺也。”釋三個;實于篚;尸不食骨體;故曰不嘗。
|
《儀禮》 | 二戴輯《禮记》 | 疏證 |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當。(《少牢》) | 曰;爲日;假爾泰筮有當。(《曲禮上》) | |
稱洗爵;献于尸;尸醋;献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有司》) | 利爵之不卒也。(《禮三本》) | 案:亦見于《荀子· 禮論》;卒作醮。利即佐食。卒即卒爵;盡饮爵中之酒。楊倞注:“醮;盡也。”義同。利獻尸、獻祝;俱無卒爵之文;故曰不卒或不醮。 |
此外;二戴所輯《禮记》中還有援引某一禮典原文並加以解說;因該禮書本已亡佚;所引原文無從核對證實。依上表所列現存諸篇之例;對其中較易辨認的章節;加以推比考訂;選擇其確鑿可信的;可列一表如下:
《儀禮》 | 二戴輯《禮记》 | 疏證 |
郊 禮 | “祀帝于郊”;敬之至也。(《禮器》) “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祭法》) | 案:郊禮爲王朝巨典;又相傅魯國也曾舉行;《郊禮》曾撰成書本是無庸置疑的。《郊特牲》是《郊禮》的傅记;都是依據原文以撰作解说的。《禮運》、《禮器》、《祭義》、《祭法》、《雜记》等篇都有记載;可以參校。(推定爲原文的加引號;下同。) |
饗 禮 | 曾子日;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雜记下》 “大饗”尚腶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郊特牲》) | 案:《雜记》所引;與《公食》歸俎于賓饰“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同。饗禮與食禮儀多相同;其爲《饗禮》原文無疑。 |
公候冠禮 | “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作;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公玄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冠》)
| 案:《士冠》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公冠》文未有孝昭冠辭及郊祝辭;明言“孝昭”;可信是部分渗入而非全篇偽作。服章儀注;與《士冠》推比;大致無誤。文不連貫;顯屬輯錄殘句。 |
《儀禮》 | 二戴輯《禮记》 | 疏證 |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玉藻》)
| 又案:“始冠”云云;見《士冠·记》而無“自諸侯下達”句;《玉藻》所引可能是《公冠记》文。 | |
天子巡守禮 | 孔子日;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曾子問》) | 案:《周禮》内宰職鄭注:“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可見鄭玄尚得見部分佚文。《曾子川》所引;當是其殘句。 |
釁廟禮 | 成廟而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云云。(《雜记下》) | 案:大戴輯《禮记》有《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孔廣森謂“皆古經之逸篇”。《雜记下》引《釁廟》全文;云“其禮”;则孔说可信。 |
根據上列二表;二戴所輯《禮记》中不僅引有十七篇原文;而且還引有已佚若干篇書本的原文;可見它的作者們手裏持有今本《儀禮》及其已佚諸篇。
《孟子》《荀子》和二戴所輯《禮记》的作者們手裏都持有今本《儀禮》及其已佚諸篇的書本;那末;這四種書的開始撰作;即是《儀禮》撰作時代的下限。
四
上文已證明《儀禮》(包括已佚諸篇)撰作于《孟子》、《荀子》、二戴所輯《禮记》之前;下面應解決四種書的撰作孰先孰後的問題。對此;除了案所周知的孟先荀後而《孟子》、《荀子》可以通過考定二人生卒年來確定其撰于何時以外;二戴所輯《禮记》的絕大部分篇章;無法知其作者爲誰;因而它的撰作早于孟、荀還是晚于孟、荀;過去一直聚訟紛紜;很難作出確切的回答。
仍然只有依照上面用過的方法;即核對四種書中有無相互引述其文來解決這個難題。
《孟子》里有二處援引《禮记》之文;《公孫丑下》篇云:
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
“父召無諾”見于《曲禮上》;“父命呼唯而不諾”見于《玉藻》;而“君命召”云云則見于《論語·鄉黨》。這些正是所謂“威儀三千”的曲禮。又《滕文公下》篇云: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扃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和《祭統》篇“諸侯耕于東郊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曲禮下》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文雖稍異而義實相同。二文都有“禮曰”;引自《禮记》是確鑿的。又《離婁上》篇云:“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高”二句見于《禮器》。云“故曰”;明引前人之語以起下文。由此可證小戴輯《禮记》的《曲禮》、《玉藻》、《祭統》、《禮器》是早于《孟子》成書的。
考孟軻生卒有二、三十家;大多數人以爲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也有人主張提前十多年;定作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卒于周赧王十二年。二說均無事實可憑;而卒年以前說較爲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傅》云:“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著書自在晚年;且在歸隱以後。周赧王三年;孟軻去齊;錢穆氏以爲“從此歸隱不復出”。錢氏又云:“《孟子》書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俱稱謚;獨宋王偃不稱謚;書中亦不見述及宋偃亡國。或《孟子》基成于魏襄王卒後、宋亡國前十年之内”(《先秦諸子係年·考辨》一二二)。其說頗精密。赧王二十九年齊滅宋;孟軻已死;而梁襄王(即魏襄哀王;《史记·魏世家》《六國表》均誤分爲襄王、哀王二世)、魯平公均卒于赧王十九年;然則《孟子》作于赧王二十年後;即魯文公初年。
二戴所輯《禮记》和《荀子》核對;既有整章整節相同;也有一二句文雖稍異而義實相同的。前者文甚冗長;不便抄錄;编列篇名對照;並加說明;輯爲表一;後者引原文對勘;輯爲表二。
表一
《荀子》 | 二戴輯《禮记》 | 說 明 |
《勸學》 |
(大)《勸學》 | 《荀子·彻學》當分:--“學不可以已”;二“神莫大於化道”;三“積土成山”;四“學恶乎始”;五“百發失一”等 |
《荀子》 | 二戴輯《禮记》 | 說 明 |
五章。大戴輯《禮记·勸學》第一、二、一三章與此篇第一、二、三章相同。(字句有出入;姑置不論。下各篇同。) | ||
《宥坐》 |
(大)《勸學》 | 《荀子·宥坐》當分:一“欹器”;二“爲魯攝相”;三“爲魯司寇”;四“觀于東流之水”;五“吾有耻也”;六“如垤而進”;七“南適楚”;八“觀于魯廟之北堂”等八章。大戴輯《禮记·勸學》第五章與此篇第四章相同。 |
《禮論》 |
(大)《禮三本》 | 《荀子·禮論》當分:一“禮起於何”;二“禮有三本”;三“立隆以爲極”;四“謹于治生死”;五“喪禮之凡”;六“以生者飾死者”;七“三年之喪”等七章。大戴輯《禮记·禮三本》全文與此篇第二章相同。 |
《禮論》 |
(小)《三年問》 | 小戴輯《禮记·三年問》全文與《禮論》第七章前段相同。(文末“孔子”至“喪也”五句二十六字不見于《禮論》。) |
《樂諭》 |
(小)《樂记》 | 《荀子·樂諭》當分:一“人情之所必不免”(至“北求之也”);二“聲樂之入人”(至“君子慎之”);三“奸聲感人” |
《荀子》 | 二戴輯《禮记》 | 說 明 |
(至“乎”);四“吾觀於鄉”;五“亂世之微”等五章。其第一章舆小戴辑《禮记·樂记》樂化章的第三、四段同;其第二章“樂者圣人之所樂也”四句與《樂记》樂施章第三段同;其第三章與《樂记》樂象章第一、二段樂情章第一段部分同。 | ||
《樂諭》 |
(小)《鄉饮酒義》 | 小戴輯《禮记·鄉饮酒義》“吾觀於鄉”-饰與《樂输》第四章相同。
|
《法行》 |
(小)《聘義》 | 《荀子·法行》當分:一“公翰”;二“無内人之疏”;三“曾子病”;四“贵玉賤珉”;五“同遊”;六“南郭惠子”;七“君子有三恕”;八“君子有三思”等八章。小戴輯《禮记·聘義》末章與此篇第四章相同而文句互有歧出。 |
《哀公》 |
(大)《哀公問五義》 | 《荀子·哀公》當分:一“論土”;“人有五儀”;三“問舜冠”;四“問哀憂”;五“紳委章甫”;六“問取人”;七”東野子”等七章。大戴可《禮记·哀公川五義》與此篇第一、二章相同。《荀子》無文末“孔子出哀公送之”七字。) |
表二
《荀子》 | 二戴輯《禮记》 |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禮論》) | 竽笙備而不和。([小]《檀弓上》) |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畢行。(《禮論》) |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大]《虞帝德》) |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禮論》) | 七十唯衰麻在身。([小]《曲禮上》)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小]《丧大记》) |
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禮論》) | 壹命齒于鄉尘;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小]《祭義》) |
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禮論》 | 日行百里。([小]《奔丧》) |
夫魚鱉鼋鼍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鹰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茍能無以利害義;则耻辱亦無由至矣。(《法行》) | 鷹鶽以山焉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鼋鼍以淵爲淺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则辱何由至哉。([大]《曾子疾病》) |
凡此等相同章節、文句;究竟是二戴《禮记》抄襲《荀子》;還是《荀子》抄装二戴《禮记》?
第一,就《樂记》與《樂論》相同之文而論;《漢書·藝文志》樂類列“《樂记》二十三篇”;《樂记正義》大題下引鄭玄《三禮目錄》云:名曰《樂记》者;以其记樂之義;此于《别錄》屬樂记;蓋十一篇合爲一篇。”又云:“劉向校書得《樂记》二十三篇;著于《别錄》;今《樂记》所断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今二十三篇之篇名俱存;其各自成篇;至爲明顯。又《藝文志》儒家煩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班固自注:“七十子之弟子。”《隋费·音樂志》載梁天監元年詔訪古樂;沈約《奏答》云:“《樂记》取《公孫尼子》”;彼時其告尚存;沈約曾加校核而後爲此說的。《史记·樂记》張守節《正義》云:“其《樂書》者;公孫尼子次撰也。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其實今本《樂记》十一篇篇次亦未嘗不爲漢人所颠倒竄亂;但前後縱有移易;文字縱有竄改;其篇爲公孫尼子原作;自無疑義。班固以 縱有移易;文字縱有竄改;其篇爲公孫尼子原作;自無疑義。班固以公孫尼子爲七十子之弟子;諸家考證;說法不一。墨翟反對音樂;而《非樂上》無《樂记》痕跡;《樂记》自出墨翟之後。荀況撰作《樂論》;目的在反對墨子“非樂”;其首“人情”章選引《樂记》樂化章的第三、四段;分成四節;每節後加“墨子非之奈何”句;最後給以總的評判:“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猶瞽之于白黑也;猶聾之于清蜀也;猶之楚而
北求之也。”其:“聲樂”章自撰其说“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云云;然後據《墨子》之说而進行辯難:“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樂者”以下是《樂记》樂施章的末段(原文末句作“故先王著教焉”);荀況稱《樂记》作者爲君子;引以駁斥墨子之说。其三“奸聲”章選引《樂记》樂象章、樂情章後;亦各加“而墨子非之”句;以下自撰其说以相駁詰。凡此引《樂记》之文;據《墨子》之说和自撰之文;界劃清楚;承轉分明;兩相對勘(文之異同;句之漏脱或顛倒;姑置不論);處處可證《樂論》抄襲《樂记》而不是《樂记》抄襲《樂論》的。樂本無經(書本);孔子甚善音樂;鼓瑟撃磐;有理論;有寶踐;其弟子後學傳述“樂之義”;到再傳弟子公係尼子始寫成《樂记》告本。其事脈絡甚明;絶無可疑之處。
第二,《鄉飲酒義》是《鄉飲酒禮》的傅记;依據經文來闡述其義的。其中“吾觀于鄉”一章冠有“孔子曰”三字;是孔子之語否固無法證實;其爲援引舊說則無可疑。《鄉飲酒禮》有用樂之節;故文中述及“工人升歌三終”云云的講樂之文。荀況錄此章以明鄉樂之義;删去“孔子曰”三字不過辨明此是舊說。如果要斷定這是《禮记》作者抄襲《荀子》;那末此章是荀況之說了;《荀子》書在;《禮记》抄錄者怎會無端加上“孔子曰”三字呢?
第三,大戴所輯《禮记》的《勸學》、《禮三本》、《哀公問五義》;小戴所輯的《三年問》;都全文(《勸學》篇除去“珠玉”一章)見于《荀子》;而《荀子》之文只是部分見于二戴所輯《禮记》。因此;僅從其文字相同上看;說《荀子》抄裂《禮记》是可以的;反之也是可以的。但是從《记》文各篇未經二戴匯輯以前單篇傳抄這一具體情況來看;當時治禮的某師抄錄《荀子》某篇中的一章當作禮類典籍的一篇來流傳;試問有何意義;因而是不可能的;而荀況抄襲《记》文某篇全文來作自撰某篇的一章;援引前人之文以增强自己的理論根據;那是很有意義的;因而是可能的。
第四,小戴所輯《禮记》之文;漢初文帝時人已有徵引。《樂记》、《祭義》並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酱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而《漢書·贾山傳》錄贾氏所撰《至言》云:“然而養三老于大學;親執酱而饋;執爵而酳;祝在前;祝鯁在後。”贾山述養老之禮是根據《禮记》的。又景、武間人也有徵引。《曲禮下》云:“天子祭大地;祭四方;祭山川;諸侯方祀;祭山川。”而《史记·六國年表》云:“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司馬遷明言“禮曰”;自是據《曲禮》立說的”。《曲禮下》又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而《史记·三王世家》引武帝元狩六年制有“支子不祭”之文;又嚴書翟等奏議云:“支子不得祭于宗祖;禮也。”也都是據《曲禮》立說的。二戴輯《禮记》在宣帝時;劉向校書得《樂记》在成帝時;文帝至武帝時已有《记》文流傅;就只能作這樣解釋;它應該與“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那樣;或有人“言记”;書誦其文而隸寫爲今文本。如果說相同之文是二《禮记》抄裂《荀子》的話;《荀子》書的撰作完成于秦王政十年以前(見下文考定);離三十四年焚《詩》《書》定挾書律;不過二十多年;那末二《禮记》在此時撰作;從時間上看是不可能的。
根據以上的辨析;斷定二《禮记》與《荀子》相同之文是荀況抄裂二《禮记》;二《禮记》禮類諸篇成書在《荀子》之前。
荀況生卒年無考。諸家異說紛紜;迄無定論。《史记·孟子荀卿列傅》云:“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壤;序列數萬言而卒。”又《春申君列傅》云:“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爲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照《史记》的說法;荀況于楚考烈王八年爲蘭陵令;爲令十七年至十五年(秦曰政九年)被廢;開始著作在秦王政九年以後;未免太晚;黄式三、錢穆均辨其不宜。《漢書·藝文志》小说家列“《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孫卿道宋子。”名家《尹文子》下颜注引劉向云:“與宋俱遊稷下。”而荀況在《天論》、《解蔽》均提及宋子;《正論》還歷引其说而辨其谬;一再说“今子宋子”;如“今子宋子嚴(儼)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師學;成文典(原作曲;據王念孫说改)”;從語氣上看;他是曾见其人而在當時即據其说以論述的。楊倞《天論》注“宋子與孟子同時”;是荀況的前輩。據此推比;有些篇章如《禮論》等;不是晚年的作品。汪中撰《荀卿子年表》;用書中所记史事來编排年表;最後见的史事是:《臣道》云:“平原君之于趙;可謂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大是之謂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此指趙孝成王九年(楚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竊符救趙事。後二年;荀況爲蘭陵令;而以後的史事不见于《荀子》。以上所列;均屬内證;據此判斷;《荀子》的撰作當在中年開始;爲蘭陵令後積極寫作;至遲在春申被殺、荀況被廢;即秦王政九年時已最後完成。
《孟子》、《荀子》書中都援引《禮记》原文;他們手中都有單篇傅抄的《记》文書本。《孟子》、《荀子》的開始撰作即是二《禮记》撰作時代的下限。孟軻早于荀況;自當以《孟子》爲準。二《禮记》禮類诸篇撰作時代的下限;不會晚于周赧王初年(魯平公之世)。
二戴所輯《禮记》徵引《儀禮》原文頗多;《禮记》禮類诸篇的開始撰作是《儀禮》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撰作时代的下限。於是;還需要論定二《禮记》禮類诸篇是什麼時候開始撰作的。
《檀弓下》載“穆公問于子思”;“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皆述魯穆公事。《檀弓上》載“子張病;召申祥而语之曰”;“申祥之哭有思也亦然”(鄭注“說者云;言思;子遊之子;申祥妻之昆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對曰;申也闻之申之父曰”;“曾子寝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孔疏“公明俄是其弟”);《祭義》裁“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孔疏“公明儀义爲曾子弟子”);所述子思、言思、曾申、曾元、樂正子春、公明儀等是孔子的第三代(孫和再傳弟子)。《檀弓上》又載“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門人問諸子思”;《祭義》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門弟子曰”;所述子上、子思之門人、樂正子春之門弟子等是孔子的第四代(曾孫或三傅弟子)。《雜记下》載:“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相由有。”據《孟子·告子下》“魯繆公之時;公明儀爲政;子柳、子思爲臣”;世柳相當于第三代;其徒相當于第四代。可見《檀弓》、《祭義》、《雜记》所載都是魯穆公以至魯共公時事;其文的撰作當在魯共公以至魯康公之世。
《檀弓上》裡有一則重要的记載:“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 小斂而撤帷。仲梁子: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撤帷。”此章引《上丧禮》始死“帷堂”而“卒斂撤帷”之文而解釋其儀的意義:曾子據禮文沐浴、飯含、襲尸、加斂衣等節認爲初喪帷堂是爲便于飾尸;而仲梁子則以意爲解;于禮文無據。二者文非問答;義又相違;二人無師承關係;自非生于同時。鄭玄《目錄》云:“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詩· 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答張逸問云:“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所稱毛公前者;不過據《定之方中》毛傳引仲梁子而作敷衍之说;稱六國魯人;雖聞于先師;亦傳說而無實證。但從語氣上看;倾向于定爲戰國後期人。《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格列仲梁子于孔穿前;樂正子、高子後;與“上下”格的公孫丑;“下上”格的齊襄王約略相當。把仲梁子當作孟軻後學;與其它记載無法合榫。總計《诗》毛序、毛傅引前人之说;只有四家五條;即《絲衣》序引高子;《定之方中》傅引仲梁子;《小弁》傅引孟子;《維天之命》、《宫》傅引孟仲子;三人都是與孟軻有交往的人物;而高子、孟仲子都不是孟軻的後學。翟灝《四書考異》云:“《韓詩外傅》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于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蓋有别。”趟岐注《公孫丑下》“尹士章”稱“齊人;孟子弟子”;注《盡心下》“追蠡章“稱“齊人;嘗學于孟子”;獨注《告子下》但稱“齊人”;趙注雖似亦有分别;不過避叟字而不及問學;其實仍指一人。因此翟氏“有别”之說;並無多大說服力。然而盖孟子公然稱“固哉高叟”;不應忽視;故趙注亦只得说“高了年長”。趟佑《四片温故錄》云:“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說最平實。高子儘管嘗來問學;其年固不嫌于較孟子爲長。《詩·維天之命》孔疏引鄭玄《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说。”劉向、應劭、趙岐均以孟軻爲子思弟子;鄭氏蓋本劉說。諸家考訂孟軻不及見子思;當從《史记》本傳“受業于子思之門人”;那末“共事子思”實是“共事子思之門人”。《公孫丑下》趟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于孟子者也。”其問學與高子相同;既是昆弟;又曾共事一師;年輩當約略相等。至于仲梁子;《韓非子·顯學》篇“有仲良氏之儒”;盧文云“良張本作梁”;即此仲梁子。鍾文烝《乙閏錄》(稿本)云“即《檀弓》及《毛詩·鄘風》傅所引仲梁子”。梁啓超云:“仲良氏無考。《孟子》稱‘陳良楚產;悦周公仲尼之道’;仲良豈陳良之字。”儒分焉八;子張、子思、颜氏、漆雕氏、孫氏(公孫尼子)、樂正氏(樂正子春)外;從時代上看孟氏和仲良氏最後;實是《孟子》書的陳良;陳良之徒陳相與孟軻問答;孟軻责以“師死而遂倍之”;則其于孟軻爲前輩。《人表》不過以高子、仲梁子見于《孟子》而未加深考;遂附列孟氏弟子之後;實不足據。錢穆氏考定孟軻在齊威王時先已遊齊;早年活動在魯康公、景公之世;仲梁子即于此時說詩議禮;《檀弓》既述其說;自不能早于此時成書。
依據上文辨證;二戴所輯《禮记》現存八十五篇;除了可以確定爲秦漢人所作以外;政類、學類並《樂记》等三十多篇撰作較早;約在魯穆公時;禮類三十九篇撰作較晚;約在魯康公、景公之際。禮類諸篇引有《儀禮》原文;可證《儀禮》撰作時代的下限應在魯共公之世;即周烈王、顯王之際;公元前四世紀中期。
前後總起來說:《儀禮》書本殘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撰作時代;其上限是魯哀公末年魯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其下限是魯共公十年前後;即周烈王、顯王之際。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到四世紀中期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後學陸續撰作的。
(原載中華書爲《文史》第十五、十六輯)
上一篇 : 礼仪中国成都区研习基地落地于成都市郫都区扬雄学会
下一篇:從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傳授